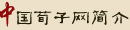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二-梁涛
梁 涛
【摘要】《荀子·性恶》所引三处“孟子曰”,应出自《孟子》外书,反映的是孟子后学“性善修习论”、“性善完成论”的思想,与孟子的“性善扩充论”有一定的差别。《性恶》乃针对《孟子》外书之《性善》篇而发,荀子批判性善论,一是认为其“无辨合符验”;二是指责其否定了礼义、圣王;三是批评其对人性的态度过于乐观。其批判的理论根据,则是“性伪之分”。
【关键词】荀子 孟子 《性恶》 《孟子外书》
二、《荀子·性恶》所引“孟子曰”疏解
《孟子》七篇中虽然有关于性善的论述,但不够集中,分散在不同的篇章之中。而外书《性善》篇,从题目上看,应是专门讨论性善,或至少有大量关于性善的论述。故荀子要批判性善论,建构性恶论,由此入手,设为靶的,自然顺理成章,简捷便利。但外书没有经过孟子的认可、审定,与孟子的思想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可能代表了孟子后学的思想,学者感慨荀子何以对孟子的性善论如此“疏隔”、“毫无理解”,恐怕原因就在这里。盖荀子所批判者乃孟子外书也,而外书成于孟子弟子,其与我们所了解的孟子思想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奇怪的。先看《性恶》所引的“孟子曰”。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
杨倞注:“孟子言人之有学,适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矫也。与告子所论者是也。”杨倞此注,十分精当,特别是联系孟、告的辩论,更是点睛之笔。杨倞所说,应该是指孟子“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之语。告子主张“性如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告子上》),认为人性好比杞柳,仁义好比杯盘;用人性成就仁义,就好比将杞柳做成杯盘。孟子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强调,将杞柳加工为杯盘,恰恰是顺应了杞柳的本性,而不是戕害了杞柳的本性。与此同理,用人性成就仁义,也是顺应了人的本性,而不是戕害了人的本性。这个性当然是指善性。由此看来,《性恶》所引的第一个“孟子曰” 虽然不见于内七篇,但并非没有根据。不过仔细分析,其与孟子的思想仍有所不同,主要是前者突出了“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学”的原因是因为“性善”,反过来讲,“性善”需要“学”来实现和完成。即,因为“性善”,所以要“学”;而“学”又促使了“性善”的实现,也就是杨倞所说的“适所以成其天性之善”。这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说苑·建本》就曾两引“孟子曰”,亦涉及到“学”的内容。
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
《说苑》所引的“孟子曰”不见于《孟子》七篇,应属于外书轶文,或类似外书的文献,反映了孟子后学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了“粪心”说和“以学愈愚”说,均反应出对“学”的重视和强调。而孟子虽然也谈及学,但他所谓的“学问之道”,不过是“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而“求放心”也就是要“思”,故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同上)。天赋予了我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要思就可以得到它,不思,就会失去它。这个“思”是反思,是“反求诸己”(《公孙丑上》),它与“孟子曰”所说的“粪心”和“以学愈愚”显然是有所不同。这说明,由于孟子提出性善论,其思想的重心转向了人的道德自觉与自主。认为人有恻隐、羞恶等四端之心,四端之心是先天的道德禀赋,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道德实践就是将四端之心“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达之天下也”(《尽心上》)。认为“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故孟子性善论也可称作“性善扩充论”,而“扩充”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是仁性的,而不是知性的;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当然,孟子也承认知性的作用,如,“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上》)这里的“闻一善言,见一善行”即属于知性活动,但在孟子这里,它是间接的、外缘的,孟子主要强调的还是内在善性(“几希”)势不可挡,“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所以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由仁义行”是内在仁义不容自已,由内而外,自主、自发的活动和表现;“行仁义”则是以仁义为客观的对象与存在,去认知、实践此外在的仁义。孟子又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尽心上》)尧舜高于汤武,故由内而外、自主自发的“性之”,高于由外而内、后天人为的“身之”。
学术的发展就是这样,思想的创新,往往伴随着形式的偏颇。孟子创立性善说,对儒学思想是一大贡献,“功不在禹下”,但他在突出道德自主性的同时,多少忽略了学、知的作用。在发展儒家仁学的同时,多少弱化了儒家的知性传统,一定程度上与孔子思想形成了反差。孔子仁、智并举,被称为“仁且智”(《公孙丑上》)。《论语》开篇就称“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孔子亦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可见其对学的重视。《论语》一书中四次讲到“博学”,谈“学”则有“学文”、“学干禄”、“学《易》”、“学《诗》”、“学礼”、“学道”等,谈“知”则有“知人”、“知十世”、“知百世”、“知禘之说”、“知礼”、“知乐”、“知父母之年”、“知所以裁之”、“知过”、“知言”等。与孔子相比,孟子可以说是仁多而智少——指经验性的“学”和“知”。更重要的是,孟子的“扩而充之”可能只适用于某些具体领域,对一切伦理、政治、社会的问题都想通过发明本心、扩充善性来解决,恐怕是不现实,也是行不通的。孟子的性善扩充说,在实践上,可能更适用于孟子这样的天赋异禀之人;在理论上,也不具有普遍性,无法应对所有的社会问题。对于这些,孟子后学不能不有所体会,并试图有所纠正。其提出“以学愈愚”,就是认为摆脱愚昧不能仅仅靠扩充是非之心,还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和认知。其提出“粪心易行”,则是要将“博学多闻”和“一性止淫”结合起来。“博学多闻”属于知性活动,“一性止淫”则属于仁性和意志活动,其中“一性”指专一其性,此性当然指善性;“止淫”指禁止其淫,意近于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故实际是回到孔子的仁、智并举,内外兼修。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和重复。在孔子那里,由于没有形成性善说,“学”与“性”的关系尚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而孟子已提出了性善论,故其后学主张“人之学者,其性善”,认为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完成性善,是围绕性善展开的,实际是将孟子的“性善扩充说”发展为“性善修习”说。荀子曾见过外书《性善》篇,他即便没有对孟学内部的变化有如此清晰的了解,对孟子后学的观点至少是知道的,故针锋相对提出“性伪之分”,对其予以批驳。荀子称: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
这里荀子对性做了两个规定,一是“天之就也”,即天的赋予;二是“不可学,不可事”。可,训为“用”。《吕氏春秋·用民》:“唯得其道为可。”高诱注:“可,用也。”《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不可学,不可事”即不用学,不用事,也就是“弗学而能”之意。而需要通过学习、从事才能实现、完成的,则属于伪。按照这个规定,上引“孟子曰”显然是犯了不察乎“性伪之分”的错误,盖经过“学”而成就的善性已不是性,而只能是伪了。再看第二个“孟子曰”。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同上)
此段文字,可谓是《荀子》研究最有争议的难点。杨倞注:“孟子言失丧本性,故恶也。”据杨注,则这段文字是持性善论的孟子在解释为何会有恶的存在。但此说显然与“孟子曰”原文不符,故学者又认为原文可能存在错漏,需改字、补字方可读通。这实际是据杨注去改原文,而没有去怀疑杨注的理解是否正确。如刘师培《荀子补释》说:“据杨说,则‘将’字本作‘恶’。改‘恶’为‘将’,当在唐代以后。”梁启雄《荀子简释》称:“据杨注‘故恶也’,正文‘故’下似夺一‘恶字’。”包遵信《读荀子札记》则认为:“‘善’疑当作‘恶’。孟子道性善,谓人之性恶,乃以其不扩充其固有之善性,而使人失丧之也。杨注谓‘孟子言失丧本性故恶也’,是杨氏所见本尚未误也。”[ 参见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注校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99页。]这样,关于此段文字,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孟子曰:“今人之性善,[恶]皆失丧其性故也。”(刘师培)
二、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恶)也。”(梁启雄)
三、孟子曰:“今人之性[恶],将皆失丧其性故也。”(包遵信)
但以上说法的最大问题,不仅是据杨注去改动原文,更重要的,是与下面荀子的议论对应不上了。在《性恶》中,“孟子曰”与下面荀子的议论是一个整体,“孟子曰”应如何理解,显然应考虑到荀子的回应。至于千年之后的杨倞注,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显然不能完全以此为据。按,上引“孟子曰”并不存在错字、漏字,应按原文来理解。今,假设连词,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五:“今,犹若也。”将,连词,犹则也。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八:“将,犹则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专则速及,侈将以其力毙。”《吕氏春秋·离俗》:“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以上两句的“将”都训为“则”。性故,指性原来、过去的状态。故,原来、旧有之意。《广韵·暮韵》:“故,旧也。”《礼记·曲礼下》:“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皆如其国之故”即皆如其国之“旧”。故上引“孟子曰”是说:若人性善,则已经不是原来的性了。该句“孟子曰”乃紧承上一句而来,上一句讲“人之学者,其性善”,认为性善是通过学而实现、完成的,那么,经过学而实现、完成的善性显然已不是本来的性了,丧失了性的本来状态,故说“将皆失丧其性故也”。可见,第一与第二句“孟子曰”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存在思想的内在关联,荀子的引用并非是随意的。那么,孟子后学的这一观点与孟子是什么关系呢?在孟子的思想是否可以找到根据呢?我们知道,孟子有著名的“四端说”,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端的本意是开端、开始。恻隐之心是仁的开始、开端,故作为“四端”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与“四德”的仁、义、礼、智显然是有所不同,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但问题是,孟子是否会认为仁、义、礼、智的获得是丧失了四端之心的本然呢?应该不会!这主要是因为,孟子持性善扩充说,他强调的是,从四端到四德需经过“扩而充之”的过程,而并非关注的是四端与四德有哪些差异和不同。在孟子那里,四端与四德的差异主要是量上的,而非质上的。但到了孟子后学这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由于提出了性善修习说,善性在实现的过程中已融入了所学、所知的内容,故最终实现、完成的性与本初、原本的性显然是有所不同了。经过“粪心”的心显然已不同于原本的心,经过“以学愈愚”性也不同于原本的性,可以说“皆失丧其性故也”。故第二个“孟子曰”实际表达的是一种“性善完成说”,认为性善有一个实现、完成的过程,由于经过了“学”与“知”,故最终实现的性不同于本初的性,“皆失丧其性故也”。“性故”指性的本然状态,“故”是对“性”的强调和说明,故说“失丧其性故也”,而不说“失丧其性也”。孟子后学的这种思想,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韩诗外传》卷五: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
《韩诗外传》出于汉初文帝时博士韩婴之手,虽然名义上依附于《诗经》,实际是杂采先秦诸子各家的著述加以编辑,主要是引《诗》以证事,而非述事以明《诗》。由于全书三分之一多的内容都可在现存先秦典籍找到出处,且有些材料自身已经用《诗经》引文作结束,故严格说来是一部编著,而不是创作。全书引用《荀子》最多,达44条,说明其对荀学较为重视。但对《孟子》也多有引用,特别是引《荀子·非十二子》文,则删除子思、孟子,只列十子,可见其不薄孟子。故徐复观先生说:“韩婴虽受荀子的影响很大,而在他自己,则是要融合儒门孟、荀两大派以上合于孔子的。”[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是符合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韩诗》持性善说,故其人性思想应主要是来自孟学,受孟学的影响要大于荀学。在《韩诗》看来,茧的性是可以抽成丝,卵的性是可以孵出鸡,但这之间都需经过一个加工、孵育的过程。而茧抽成的丝,显然已不同于茧;卵孵出的鸡,显然也不同于卵,可以说“皆失丧其性故也”。这说明,“孟子曰”的表述没有问题,相反杨注的理解则是不正确的,《韩诗》“茧之性”、“卵之性”的说法可能就受到孟学人性论的影响,或是对其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理解,才能与下面荀子的回应对应起来。据《性恶》,荀子的回应是:
曰:若是,则过矣。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
该段文字的难点在于“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一句,以往学者多将该句的“生”理解为出生,故认为是说,“言人之性,一生出来就离其质朴,离其资材,那么,其质朴之美与资材之利的丧失是必然的。”[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543页。]或认为是,“如果人的本性生下来就脱离了它固有的自然素质,那就一定要丧失本性。”[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2页。作者可能感觉到以上解释不通,又补充说:“荀况认为,人的本性是不可能脱离‘资’、‘朴’的,而‘资’、‘朴’是‘好利’、‘疾恶’、‘有欲’的。”]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荀子那里,所谓“朴”、“资”就是指人生而所具的禀赋,若说生下来就失去了先天禀赋,显然是自相矛盾,根本不通的。按,此句的“生”不是“出生”之生,而是“生长”之生,该句是说:若人的性,在生长、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先天的朴和资,就不再是性了。因为“孟子曰”认为性善乃“失丧其性故也”,故荀子争锋相对,认为性只能是就朴、资而言,丧失了朴、资就不能算是性了。在荀子这里,性、朴、资是同一的概念,也就是“孟子曰”所说的“性故”。在荀子看来,只要搞清了什么是性?性善、性恶就根本不用争论了,是非常清楚的。这当然还是从其“性伪之分”来立论的。荀子接着讲:
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这段文字是对“孟子曰”的进一步回应。由于孟子后学认为,经过学、知而实现、完成的善性,已不是原来的性了,“失丧其性故也”。故荀子指出,不是这样!如果主张性善,一定要就其朴和资而言,不离开朴就是美的,不离开资就是好的,才可以说是性善。性与善的关系,就如同眼睛与视觉、耳朵与听觉的关系一样,有了眼睛就能看,有了耳朵就能听,不需任何的学习、培养。同样,不离朴、资就可以表现出美、善,才能算是性善,若经过后天学、知的培养,就已经是“伪”而不是“性”了。这样,荀子便从“性伪之分”对“孟子曰”进行了批驳,同时说明,“孟子曰”一定是在讨论性善的问题,而与恶无关。今人据杨注将“今人之性善”改为“今人之性恶”,或是在“皆失丧其性故也”一句中加“恶”字,都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一个“孟子曰”相对简单,只有一句:“孟子曰:人之性善。”但这一句同样值得关注。在《孟子》七篇中,尚没有以命题形式对人性做出明确判断,只是提到“孟子道性善”、“言性善”。而“道性善”、“言性善”是宣传、言说关于性善的一种学说、理论,它虽然也肯定“人之性善”,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后者。这是因为“人之性善”是一个命题,是对人性的直言判断,而性善论则是孟子对于人性的独特理解,是基于孟子特殊生活经历的一种体验与智慧,是一种意味深长、富有启发意义的道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道理”显然是不能用“人之性善”这样一个命题来概括的。[ 笔者曾经提出,孟子性善论实际是以善为性论,“孟子道性善”的深刻意蕴至少应用“人皆有善性”、“人应当以此善性为性”、“人的价值、意义即在于其充分扩充、实现自己的性”三个命题来概括。参见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孟子后学由于提出“人之性善”,以命题的形式对其论点做出概括,一方面固然使其主张明确化,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分歧与争议。据王充《论衡·本性篇》: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谓人生于天地,皆禀善性,长大与物交接者,放纵悖乱,不善日以生矣。
据王充的介绍,《性善》篇认为“人之性善”是因为人“皆禀善性”,这与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此天之所与我也”(同上)的看法,显然是一致的。但《性善》篇又称“人性皆善”,则容易引起分歧与争议,与孟子的思想也不完全一致。孟子除了肯定人有仁义礼智的善性外,也承认“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尽心下》)等感性欲望事实上也是性。只不过通过“性命之分”,主张“君子不谓性也”(同上),又将其排除于性之外。但只是一种价值选择,且仅限于君子。所以,孟子并没有“人性皆善”的表述,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王充的转述无误,“人性皆善”便不能没有争议。《性善》篇的表述或许与其“人之性善”的命题有关,因为“人之性善”就是认为,人性的内容及其表现是善的。从命题上肯定了“人之性善”,自然就会得出“人性皆善”的结论。另外,《性善》篇除了肯定性善外,还对恶或不善做了说明,认为是“物乱之也”,即外物的引诱和扰乱,这与孟子“陷溺其心”(《告子上》)的说法一脉相承。前面说过,荀子《性恶》篇乃针对外书《性善》篇而作,因后者主张性善,故荀子主张性恶;因后者有“人之性善”之说,故荀子针锋相对提出“人之性恶”。不过据王充所述,《性善》篇实际涉及两方面的内容,既肯定了性善,也对恶或不善的原因做了说明。与之相对,荀子的《性恶》篇也谈到了善、恶两个方面,既肯定了性恶,也对善做了说明,其完整的表达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