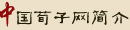原标题: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论《礼论》《正名》《性恶》的性-伪说
编辑注:文章()是上图“伪”字
三、《性恶》的性恶-善伪说
与《礼论》《正名》不同,《性恶》专门讨论人性论问题,故文中多次使用“伪”,[ 《性恶》共使用“伪”29次,其中“积伪”5次。另有“诈伪”1次,不计算在内。]并以伪说明善,实际是提出了性恶善伪说。虽然《礼论》已经性、伪对举,但其伪是“文理隆盛”,是外在的礼仪、仪节,而并非内在主体,故“无伪性不能自美”,美是礼仪饰性的结果。《正名》虽然从内在主体的角度理解伪,对伪做了两层定义,但并没有讨论性与伪的关系。只有到了《性恶》,才从性、伪的角度对人性善恶做了讨论。《性恶》开篇称: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注:又)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注:导),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从《荀子》一书来看,《性恶》的特殊性在于,一是提出性恶,二是主张善伪。关于性恶,学者已注意到《荀子》一书只有《性恶》提出性恶,其他涉及人性论的各篇并没有性恶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之前的各篇中性与欲并不完全等同,荀子所理解的恶主要是来自欲,而不是性。如《富国》认为“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但又认为放纵欲望不加节制,不仅导致争夺、混乱,而且还会“害生(性)”,故欲可为恶,而性不恶,盖因为性乃规范性概念。《礼论》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也是认为欲可以导致恶,但并不认为性本身是恶,反而提出“性者,本始材朴”,性是原始素朴的,包含了吉凶忧愉之情甚至爱,其本身不是恶。从荀子思想的发展来看,其提出性恶,主要是将性等同于欲,以欲来理解性,性不再是规范性概念,而成为描述性概念,性恶由此始得以成立。这一转变在《正名》已经开始出现,而到了《性恶》才真正完成,故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注:又)好声色焉”,将人之欲望中“好利”、“疾恶”、“好声色”这些明显属于恶的内容明确归于性,认为是“今人之性”生而具有的。故《性恶》之所以提出性恶,首先,是将性看作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如《富国》《礼论》等将性、欲有所区别,虽然认为欲可能导致冲突、争夺也就是恶,但性本身不是恶,相反,“纵欲”还会“害生”,也就是害性。其次,是突出了“好利”、“疾恶”、“好声色”这些欲望中属于恶的内容,好利就其会导致冲突、争夺而言,显然可以看作是恶的,或至少可能是恶的;疾恶也就是嫉妒憎恶是一切纷争的根源,当然是恶的;耳目之欲可以是中性的,但加上好声色则显然是恶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一书中,只有《性恶》将好利、疾恶、好声色并列,并以此说明“人之性恶”。《荣辱》肯定“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但没有说明就是性;《王霸》提出“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类似于好声色,但认为这是“人之情”而非性;除《性恶》外,《荀子》其余各篇均没有将疾恶归于性或者情和欲。故性恶说的成立,实际与《性恶》对好利、疾恶、好声色等人性中恶的突出和强调是密切相关的,而这在其他各篇中是没有的。还有,是提出“顺是”,认为顺从好利、疾恶、好声色的流露而不加节制,必然会产生“争夺”、“残贼”、“淫乱”等恶的后果,故有学者认为,荀子是从行为结果来看待人性善恶的。但结果都是由原因造成的,根据《性恶》对恶的定义:“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偏险侧重于原因,悖乱强调的是结果。以此衡量,好利、疾恶、好声色显然是偏颇、危险的,属于恶端,而其所造成的“争夺”、“犯分乱理”以及暴力是悖理、混乱的,属于恶果,故荀子的性恶说亦可称为性有恶端可以为恶说。
再来看“其善者伪”。杨倞注:“伪,为也,矫也,矫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 [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第289页。]伪是作为,具体讲是矫正,是对本性或天性的矫正。结合上文内容看,其所谓伪应是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即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其所矫正的是人性中的好利、疾恶、好声色,以达到“辞让”、符合文理以及治理的结果,也就是荀子所理解的善。因此,杨倞释伪为矫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矫乃是一种强制,一种外在的教化和引导,对于荀子而言,善的形成还需要内在的自觉和主动。《性恶》接着称: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注:行)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在这里,一方面是古之圣王有鉴于人性之恶,“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便“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另一方面则是“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前者是教,后者是学;前者是从古之圣王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礼义文化传统,后者是今之人对于礼义文化传统的接受、认知和学习,古与今是对应的。故在荀子看来,善的养成固然要以圣王的礼义、师长的引导为条件,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选择、努力的结果,成为君子还是小人最终还是取决于自己。只不过在荀子那里,人是社会的存在,不能脱离礼义文化传统,需要在学习、实践礼义的过程中成就、完善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师长的指导、法度的约束自不可少,当然更重要的是个人对学术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对礼义的实践。故在这段文字中,“其善者伪”的“伪”既指外在的矫,也包括了内在的学,矫与学是相辅相成、内外统一的。而“善”,《性恶》的定义是:“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正理也就是正确、合理,平治也就是治理、有序。具体到以上两段文字,主要指圣王所制定的礼义、法度,人们遵从礼义、法度所表现出的辞让、忠信、文理等品质,以及最终所达到的社会治理。故荀子的善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概念,其实现需要外在的条件,需要圣王的制作,文化的积累,是第一代代人思虑、探索、实践的结果,不是仅凭个人的主观努力就可以的。因此,性本身不可能是善的,善是通过伪而实现的。“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性恶》)这种说法就颠倒了性善与为学的关系,不是因为性善,所以才需要通过学习去进一步实现、完成善,而是善根本就是来自伪,不是性本身所具有的。“孟子曰”的错误在于“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根据荀子的规定,“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是上天的赋予,不是通过学习、努力获得的。礼义是圣人制作的,是需要经过学习、努力才能够掌握的。“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注:当为‘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不通过学习、努力就可以获得,属于天然的就是性,需要经过学习、努力才能获得,属于人为的则是伪。按照这种规定,性当然不可能是善的,只能滑向恶,而礼义作为善只能是来自伪,来自心的思虑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性恶》中伪是指制作礼义的能力——但仅限于圣王、圣人,而不是礼义本身。对于礼义,《性恶》往往称为“积伪”,且与“礼义”并列,如“礼义积伪”,而不直接称为伪。故在荀子那里,伪主要指主体心或者知性的活动和运用,表现在制作和学习、实践礼义等活动之上。从这一点看,性、伪之分实际来自《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二分,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
在《富国》等篇中,荀子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情性、知性的不同特点,以及将二者笼统称为性所存在的问题,故在《正名》中通过对性的两层定义,一方面将情性、知性(指能知)在理论上都涵盖在性的第一层定义中,另一方面又将智性(指所知)排除在性的第二层定义之外,将性限定为情性,而将智性归为伪。伪既指“心虑而能为之动”,也就是心的思虑活动,抉择判断,也指“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也就是心在实际运用中所获得的能力、品质或习性。这样,伪在荀子那里就成为涵盖能知与所知,兼具知与能,既能创造善,又能认知、实践善,表达人之道德主体性的重要概念。由于荀子的善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最终要落实在社会治理上,故不说伪()或者心的活动就是善,而说善是来自伪或者心的思虑及活动。但这实际表明,伪()或者心的活动是趋向善的,是可以为善的。性与伪正代表了人生的两种力量,一个趋向恶,一个朝向善,荀子就是从这种张力关系中对人性善恶做出考察。《性恶》称: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好逸恶劳的,但人们却往往“见长而不敢先食”,“劳而不敢求息”,这就是因为心的抉择判断或者伪的作用。虽然“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违背性,但人们通过心的作用,认识到它是“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具有合理性,就可以“反于性而悖于情”,选择与情性相反的辞让了,性与伪正构成人生中两种不同的力量。又例如,“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兄弟相拂夺”是“顺情性”,“让乎国人”则是“化礼义”也就是伪的结果。性与伪正好相反,一个将人拖向恶,一个将人拉向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性恶》称“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人的生命中本来就存在向善与趋恶两种力量,二者是一种张力关系,当人滑向恶时反过来也会促使其向善,就好比一个学生因为偷懒而成绩下降,反而会促使其发奋努力一样。[ 参见拙文:《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5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 性“无礼义”、“不知礼义”,但人又能“强学而求有之”、“思虑而求知之”,这就是因为人有心,心可以为——伪()。在上引文献中,由于荀子没有点明“化礼义”、“思虑而求知之”等与伪的关系,只是在“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的结论中予以说明,故往往使人们无法认识到二者的关系。但“化礼义”等属于伪,应从伪来理解则是肯定的。明乎此,则以上文字便可豁然贯通了。其实,荀子在《性恶》中明确肯定“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种人人所具的“知仁义法正之质”和“能仁义法正之具”显然是生而所有的,属于性(第一义)的范畴,可归于心,是人们认识、实践“仁义法正”也就是礼义的内在禀赋和能力。只不过“质”、“具”是静态的概念,其优点是点出了与仁义法正的关系,其不足是无法像伪一样动态表达主体心的实践过程,故可以结合质、具来理解伪,伪是人们认识、实践仁义法正或礼义的内在禀赋和能力,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获得的品质或习性。唯有此,才能真正把握伪的精神实质,理解其作为表达荀学道德主体性概念的全部内涵。
既然荀子人性论的完整表达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那么就容易回答“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的疑问了。本来人就有性与伪()两种禀赋、倾向或能力,就礼义而言,它并非来自性,而是来自伪。这就好比,“陶人埏埴(注:用水和土)而为器”,“工人斫木而成器”,这些器具“非故生于人之性”,不是来自人的天性,而是通过创造发明、学习实践而制作的,这种创造发明、学习实践就属于伪。同样的道理,圣人制作礼义不是来自他的性,而是来自他的伪,也就是来自心或者知的思虑活动,与《富国》的“知者为之分也”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不过荀子以圣人之伪说明礼义的产生,不仅有夸大圣人作用的嫌疑,在理论上似也有自相矛盾,引人误解的地方。既然“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而“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圣人不同于众人不在于性,而在于伪。这个“伪”显然并非指心之能知而言,而应是指所知,指心之运用,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故圣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学习、积累的结果。“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这样一方面礼义产生于圣人之伪,另一方面圣人之伪又是学习、实践礼义的结果,那么,在礼义产生之前,圣人又是如何“化性起伪”进而制作礼义的呢?这就是所谓荀学研究中第一个圣人如何制作礼义的难题。其实从儒学史看,荀子之前的儒者一般都不认为礼义是圣人个人的创造,是圣人个人智慧的产物。孔子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故在孔子看来,礼乃是在历史的损益沿革中自生、自发形成的,是千千万万个人思虑、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某一个人的创造。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明确提出“《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礼、乐,有为举之也”,“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礼开始都是生于人,具体讲是生于人情,是人情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圣人的作用只是在于对于礼义的整理、修订和完善,但礼义“其始出皆生于人”。荀子忽略了礼义“生于人”的一面,过分夸大圣人的作用,不仅使礼混同于法,堕入权威主义,也使其在理论上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可以说是荀子思想的一个不足。其实,荀子自己也承认礼义最初是人们思虑、选择的产物,是自发形成的,只是不够明确和充分而已。他说“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这里的“思虑”不仅指圣人的,也包括他人思虑,故说“积”,而“伪故”是礼义产生之前社会上自发产生的行为规则。[ 参见拙文:《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中国哲学史》2013年3期。]“圣人”在总结思虑、学习伪故的基础上进一步“生礼义而起法度”。因此,即使圣人也不能凭空制作礼义,而必有所因袭、承继,圣人之伪是以人们的伪故为条件的。故荀子又有“化性起伪”之说,认为人经过化性起伪方可成为圣人,成为圣人方可制作礼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同上)化性,变化性。据荀子的定义,“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正名》),而性主要指欲望而言。故化性不是“去欲”、“寡欲”,不是否定欲,而是“道欲”、“节欲”,是引导欲,节制欲,包括消除其中不好的内容,如疾恶、好声色等。[ 黄百锐(David B. wong)说:“道德不是消除非道德的感性欲望,而是把它们限制在一定程度,使其与道德化的情感、欲求相适应。”(David B. wong: “Xunzi on Moral Motivation”, in T. C. Kline and Philip J. Ivanhoe eds,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Hackett Pub., 2000,p151)对于一般的情感欲望而言,荀子是主张节制、引导,但对《性恶》的疾恶、好声色等恶性而言,荀子则应是主张消除的。黄说忽略了恶欲与一般欲望的不同。]起伪,出现伪。包括第一义的伪()和第二义的伪,或者说经第一义的伪()而落实为第二义的伪。在荀子那里,化性是社会习俗、行为对人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由于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故首先面对的是化性的问题。《儒效》称:“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注错,举措,也就是行为。农夫有农夫的举措,工匠有工匠的举措,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性,包括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情绪感受和欲望爱好等。习俗,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性。但如学者指出的,“‘注错习俗’显然可以有对错之分。正确的‘注错习俗’可以使人成为君子、圣人,错误的‘注错习俗’则使人成为小人,甚至桀、跖这样的大奸大恶之辈。”[ 邓小虎:《〈荀子〉中‘性’与‘伪’的多重结构》,《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评论》第36期,2008年;又见氏著:《荀子的为己之学——从性恶到养心以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因此,化性是中性的,只是强调“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即行为、习俗对人的客观影响,并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判断和选择,故荀子又提出“并一而不二”也就是专一,主张“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强调对于举措、习俗要有审慎的态度,“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只有充分、全面积累善才可成为圣人。《儒效》只说到化性,而没有提到起伪,年代应早于《性恶》等篇,在思想表达上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不论是“并一而不二”也好,“谨”、“慎”也好,都不足以表达人的道德选择和判断。《性恶》则提出伪,以伪说明道德主体,较之《儒效》的专一显然是一种发展。由于人有心、有知,面对化性也就是行为、习俗的外在影响,可以做出判断、选择,这就是“起伪”。[ 克迪斯·海根(Kurtis Hagen)认为,道德教化并没有转化“性”,而是在其上“增加”了一个新的“辅助性动机结构”(auxiliary motivational structure)。荀子提供的教化方法不是去转化“原初自私欲望”,而是去结合“原初自私欲望”与智慧,让人们藉由有意识的努力,发展出一个新的辅助性动机结构来改变人们的性格。见Kurtis Hagen, “Xunzi and the Prudence of Dao: Desire as the Motive to Become Good,”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0.1 (2011): 53–70。海根认为化性并不是消除欲望,而是新增加了一个动机结构(引者注:实际应理解为心的活动),是正确的。但他认为道德教化并没有转化性,则不准确。对海根的批评,可参见王华:《礼乐化性:从〈荀子〉谈情感在道德认知与判断中扮演的角色》,见郑宗义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13辑,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第39~68页。]伪需要结合心去理解,尤其是第一义的伪()。心学习、实践外在习俗、伪故以形成内在品质或习性,这就是“伪起”。在此基础上,方可“生礼义而起法度”,圣人制礼义与习礼义以成圣人本来就是统一的。故在荀子那里必须承认和肯定习俗与伪故的存在,习俗与伪故都不是圣人制作的,但却是圣人成为圣人进而制作礼义的条件。《性恶》缺乏这一环节或表述不够明确,故容易引起种种误解和指责。但《大略》篇则提出,“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礼不一定要记录在典册之中,只要符合、顺应人心的都是礼。这种礼显然是人心选择的结果,表现为习俗、伪故,而不是某个圣人的制作。又,“舜曰:‘维予从欲而治。’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从欲而治”也就是从民欲而治,因为礼是为了使庶民百姓满足、实现其欲望而达成的度量分界,故以礼而治也就是从欲而治了。这种礼普通平常,“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显然不是为成圣的目的设立的,但成为圣人必须从学习这种礼义开始,不学则不成。学术界一般认为,《大略》为荀子弟子记录的荀子言行,是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的史料,以上两则可能是荀子晚年的思想,其“顺人心”说是对圣人制礼说的补充和完善,不仅圣人制礼需要以习俗、伪故为条件,成为圣人也是通过学习、实践习俗、伪故得以实现的。
总括而言,荀子《礼论》等篇中的性-伪说是对《富国》等篇情性-知性说的继承和发展,在《富国》等前期作品中,荀子将知也称为性,与情性并列,形成所谓二重结构。但知包括能知和所知两个方面,前者是生而所具的认知能力,后者是此能力的实际运用和表现,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将二者都笼统称为性,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如将属于所知的“异知”也称为性等。故在《礼论》《正名》《性恶》等中期作品中,荀子不再称知为性,若涉及相关内容,也改称为“质”或“具”,如《性恶》的“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同时又提出伪,以伪综括能知与所知,作为表达主体认知和实践活动的重要概念。从这一点看,伪是与心密切相关的概念,在《富国》《荣辱》等篇中,心还不是严格的哲学概念,心只是一心理器官,指感觉欲望等。而到了《正名》等篇,则已然将心视为重要的哲学概念了,并对心的性质、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如“心有征知”,“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心之所可中理”,“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正名》),“专心一志,思索孰察”,“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性恶》)等。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显然与荀子思想的深化,尤其是伪概念的提出是密切相关的。
荀子对伪的理解和使用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在《礼论》中,伪是“文理隆盛”,指外在的礼仪、礼节,而非内在的道德主体。《正名》通过对伪的两层定义,将伪限定为内在道德主体,其中第一义的伪指心的抉择、判断及活动,第二义的伪指心经过认知、实践所获得的品质或习性。从第一义的伪到第二义的伪,需要以外在的礼义积伪为条件,这反映了荀子道德智虑心与孟子道德本心的不同。荀子的心虽然好善、知善、行善,具有道德功能和属性,但需要向外探索和认识,以发现实现善的知识和方法;孟子的心则具有良知、良能,只要扩充本心就可以达到善了,故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性恶》则全面系统地以性-伪说解释、说明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将性归于恶,以伪说明善,从善、恶的内在张力对人生做出考察,实际提出了性恶、善伪说,由于伪与心密切相关,也可称为性恶、心善说。不过荀子似乎没有将其人性论贯彻到底,他一方面认为人既可以追求善,也可能滑向恶,甚至提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似乎只有少数圣王不仅会选择善,而且会规定善,而大多数民众若没有圣王的引导则必然会走向恶。这样,一部分人具有道德自主、意志自由,另一部分人则意志软弱、道德无力,必须接受他人的教化和引导,实际将抽象的哲学问题与具体的政治主张混同在一起。与此相关,《性恶》中的伪既指圣王对于民众的教,也指“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注:行)礼义”的学;既是从一般哲学角度表达道德主体的认知、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又结合了具体身份表达了圣王、师长与“今之人”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凡此种种,难免都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和质疑。
另外,《礼论》等篇虽然都是从性-伪的角度讨论人性问题,但对人性的具体理解也存在着发展变化。《礼论》的性指“本始材朴”,具体内容则包括吉凶忧愉之情以及爱,基本属于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虽然将爱归为性不是荀子的主要观点,但在荀子人性思想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特别关注。现学术界有学者主张用性朴论代替性恶论以概括荀子的人性论主张,显然是对性朴做了抽象理解,而没有考虑其具体内涵。若结合《礼论》的内容,所谓性朴是指我们在吉凶事物时所表现的快乐、忧愁之情,以及对于亲人的哀痛之情,往往是率真、质朴,不加掩饰的,故需要礼节、仪式的修饰、完善,这就是“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者,文理隆盛也”的含义所在。它无疑是荀子对于人性比较独特的主张,是根本不能概括其整个人性论思想的。《正名》上半部分对性做了两层定义,内涵比较复杂,其中第一义的性不仅包含情,理论上也可以包括知甚至爱,第二义的性则限定为好、恶、喜、怒、哀、乐之情。不论第一义的性,还是第二义的性都没有性恶的观念,相反提出“性伤谓之病”。《正名》下半部分主要从生理欲望理解性,性也开始从规范性概念向描述性概念过渡和转变。到了《性恶》,这一转变已经正式完成,性不仅等同于欲,成为描述性概念,而且以好利、疾恶、好声色言性,由此性恶始得以成立。学者注意到《荀子》一书中只有《性恶》明确提出性恶,故认为其人性主张是比较特殊的,但结合荀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其人性论发展的内在轨迹和线索。杨倞说荀子“激愤而著此论”,[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第2册,第289页。]故有学者推测,刺激荀子撰写《性恶》的可能就是长平之战,在目睹故国的失败、战争的血腥、人性的残暴之后,荀子激愤地喊出性恶,从人性的角度对“当战国时,竞为贪乱,不修仁义”的现状做出批判和反思,同时提出“其善者伪”,认为人仍然有追求善的内在根据和动力,对人生并不完全失去信心,并寄托于圣王的出现。长平之战结束于公元前260年,荀子约76岁,若以上推理成立,则《性恶》当属于荀子中期偏晚的作品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