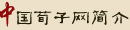原标题:
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论《修身》《解蔽》《不苟》的治心、养心说
三、《解蔽》的“治心之道”
与《修身》不同,《解蔽》言心而不言气,尤为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者乎!”心不发挥作用(“不使”),则不能正常认识外物,况且被错误的观念支配呢(“况于使者乎”)?因此,心固然重要,但首先要解除蒙蔽,认识道。其实现实中那些“乱国之君,乱家之人,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他们的本意也无不是想找到正确的治国之道,只是由于“妒(注:或谓当为‘误’)缪于道而人诱其所迨(注:通‘怠’)也”(《解蔽》),结果是“蔽于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可见,即使有好的愿望,但如果不认识道,同样达不到治国的效果。“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同上)从认识的角度看,“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世界是复杂的,存在着欲恶、始终、远近、博浅、古今的差别,但人们往往只从自己喜好或熟悉的角度看问题,这样偏于一端便会产生各种蔽。圣人看到认识的局限,蔽塞的祸患,排除认识的局限,不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而是全面考虑到事物的整体,并在其中设立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同上)荀子的“虚壹而静”既是指心的功能,也指治心的方法。在荀子看来,心虽然能虑、能择,但其所选择不一定合于道,还需要通过治心的方法,排除成见、专注如一、保持平静以知虑明,使心合于道。《解蔽》称: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盘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
“处一危之”的处,意为处在,这里是遵循的意思;[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6页。]一,指“壹于道”,也就是专一于道;危,戒惧;之,代词,指外物的干扰与影响。“养一之微”的之,训为至。《玉篇·之部》:“之,至也。”微,精微。[ 徐复观说:“‘道心之微’的微字,似乎含有两层意义:一是因心知道以后,而心的认识能力,可极尽其精微。二是因认识之极尽其精微,而可以知行冥一,由知之精而同时即见行之效,有似于《中庸》所说的‘从容中道,圣人也’的微妙境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4页。]故“处一”,是努力遵循于道的阶段,故需戒惧;“养一”,是已与道融合为一的阶段,故曰精微。李涤生说:“‘人心’,谓常人认识心。此心易蔽,惟专一于道,时加戒惧,则不蔽。‘道心’,谓化于道之道德心。由戒惧其心,道心日长,至于涵养纯熟,认识精微,而化于道,即为道德心。此言:由人心之戒惧,可至道心之精微。”[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492页。]故以上文字仍主要是从心知道的角度来立论的,属于虚壹而静的范畴,而“其荣满侧”一句表明,荀子对人心之戒惧实际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是心知道的必要环节。人心之所以戒惧,是因为“人心譬如盘水”,一旦受外物的影响,就难以“定是非,决嫌疑”,故需要“导之以理,养之以清”。另外,一心不可二用,“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故需要保持心的专注如一,如此方可以知道。
需要说明的是,《解蔽》的虚壹而静只是“知道”的方法,是需要以“求道”为条件的,故说“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谓之”,告之。故只有对未得道而想要求道者,方可告知以虚壹而静。同样的,也只有那些想要求道者方可通过虚壹而静而知道。至于“求道”、“思道”则是意志的抉择,是虚壹而静的前提,而不是虚壹而静的结果。徐复观先生将荀子知道的过程概括为:求道→心虚壹而静→心知道→微,[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16页。]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故在荀子那里,既有虚壹而静的方法,也有求道的功夫;前者是知虑明,是知的方法,后者是志意修,是志的功夫,二者结合,心方可知道,并达至精微的境地。对于意志的塑造和培养,《解蔽》也称为“治心之道”: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 原文作“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据文意改。]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注:尽)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觙”应是伋的通假,暗指子思孔伋。“善射”的“射”指射覆,古代近于占卜的游戏,在器具下覆盖一物,让人猜测;以,而,表并列关系;“好思”的“思”,从下文看,应是指思仁。据竹简《五行》,子思重视思,且有神秘体悟的特征,如“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察则安”等,故与射覆联系在一起。以上文字实际是以孟子、有子、子思为例,说明立志、求道的方法。孟子担心败德而休妻,可以称得上是“自强”,但还没有反省到内心的仁——这当然是就孟子早年的经历而言。有子担心昼寝而以火灼掌,可以称得上是“自忍”,但还不能说是发自内心的喜好。子思喜好反省内心的仁,有一套思仁的方法,但必须“辟耳目之欲”,“远蚊虻之声”,故可称得上是“危”,但还没有达到精微的境地。真正达到精微的是至人,他们无需自强、自忍、自危,却能从其欲,尽其情,又符合理,能够以理制情。“制焉者理矣”的“焉”,代词,指欲和情。故“纵其欲”三句实际是说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从容中道。以上文字有几点值得重视,首先,不论是孟子的自强、有子的自忍,还是子思的“辟耳目之欲”,都是为了立志、求道,是意志的塑造和培养,与前面的“虚壹而静”有所不同,二者属于不同的功夫和方法,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其次,荀子认为立志、求道的关键是“思仁”,孟子出妻、有子灼掌虽然难能可贵,但还不是从思仁出发,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和喜好,故要逊于子思。子思虽然喜好思仁,但还需要借助外在的手段,如“辟耳目之欲”等,只有在“闲居静思”时才可以通达,所以同样没有达到精微的境地。真正代表荀子理想的是至人,他们不借助外在手段,只向内用心,就能从容中道。这里“浊明外景,清明内景”两句十分关键,有助于理解荀子的思想倾向。《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指发光于外;“含气”,反光于内;景,同“影”。火、日发光,照事物形影于外,金、水所成之镜反光,照事物形影于内。荀子用“外景”表示用心于外,考察外物;用“内景”表示用心于内,反求诸己。前者是“浊明”,是内暗外明,是表面的明;后者是“清明”,是内外透彻光明,是真正的明。荀子的“浊明外景”应是指孟子、有子、子思自强、自忍、自危的功夫,而“清明内景”应是指至人思仁的方法,它超越了强、忍、危,不再需要外在的激励或手段,真正达到精微的境地。故荀子也将至人与仁者、圣人并称,在其看来,他们实际也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做到思仁的人。不仅如此,荀子还称“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认为只要做到思仁就可以从容中道,这里的道当然是就礼义而言,指礼义之道。故是认为只要思仁,掌握了仁,就可以实践礼,从容中道,实际是突出了仁的地位和作用,较之其以往的思想无疑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荀子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至于仁与心是什么关系?是否可归于性?这一问题虽然已蕴含其中,但《解蔽》尚没有给出明确的讨论和说明。
《解蔽》应是荀子在稷下学宫晚期的作品,其内容明显受到各家学术思想的影响,其中虚壹而静受到稷下黄老道家的影响,其对于虚、壹、静的理解和论述在《管子》、黄老帛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表达,这点已有学者指出。[ 参加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8~292页。]其对思仁的强调则受到子思的影响,而“仁者之思”、“圣人之思”的表达类似于《五行》篇的“仁之思”、“圣之思”。其将仁内在化,诉诸神秘的内心体验,与荀子之前经验化的特征明显不同,出现了政治化仁学向心性化仁学的转变。其对子思、孟子的评价虽然有所保留,但与《非十二子》篇直斥“子思、孟轲之罪”的态度存在明显反差。《非十二子》为荀子前期或“始来游学于齐”时的作品(详后),《解蔽》则完成于游齐的晚期,这说明荀子晚年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之前对思孟之学的态度,不再视为水火,而是有意地借鉴、吸收,并对以往的思想进行调整。荀子晚年出现这种思想的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关注意志的塑造、培养,以及道德主体性的确立密切相关的。
四、《不苟》的“养心莫善于诚”
《解蔽》之后,《不苟》也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不过《解蔽》的治心强调的是仁,而《不苟》的养心突出的诚。《不苟》开篇提出“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谓“当”是指“礼义之中也”,也就是符合礼义或道。在这一问题上,君子与小人正好相反。“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大心,心志广大;小心,心志狭小,二者属于意志的活动,与属于知能的智、愚相对。志向可大可小,知能可智可愚,这些可以是中性的,故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不在于意志、智能本身,而在于心术的善恶,在于是否志于善和遵循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苟》提出了以诚养心说: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注:同“默”)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注:则)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此段言诚,颇类《中庸》《孟子》。此为荀子书中最特别之一段”。[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197页。]而如何理解此段文字,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蔡仁厚说:“上文通过‘诚’而言‘心’,实与荀子之思想不甚一致。与荀子思想一致的养心之道,当从《解蔽》篇所谓‘虚、壹、静’的工夫上说。……有了虚壹静的大清明之心,以之通观万物则可以知其情,以之参稽动乱则可以通其度,以之经纬天地则可以裁制万物,使之各得其宜,各尽其用。”[ 蔡仁厚:《孔孟荀哲学》,第489页。] 但此说显然忽略了荀子的养心实际包括知虑明和意志修两个方面,而仅以前者为养心的内容,故有此悖谬之论。其实《不苟》的以诚养心,“其重点在于‘心’和‘志意’的持守。‘诚’指一种‘真实’的心灵状态……这种‘真实’指的是‘心’真实地接纳‘道’为一贯的指导原则,并奉行持守其实质内容‘仁义’,因此能在‘志意’上固守‘仁义’,并在‘身行’方面实践‘仁义’,从而做到表里如一、内外贯通”。[ 邓小虎:《荀子的为己之学——从性恶到养心以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0页。]故《不苟》的以诚养心并非与《荀子》其他各篇的思想完全相悖,而是可以在《修身》的“治气养心之术”、《解蔽》的“治心之道”中找到思想联系,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专门提出诚而已。而“诚”也就是《中庸》《孟子》中的诚,这说明《不苟》与《解蔽》一样,也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反映的是荀子思想晚年的发展和变化。《不苟》上引文字在《荀子》三十二篇中之所以备受争议,正可以从这一点去理解。
已有学者注意到,上引文字中论以诚养心一段,颇近于《中庸》第23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但《中庸》是说“致曲”,而《不苟》是说“养心”,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致曲,致,推致;曲,郑玄注:“犹小小之事。”孔疏:“犹细小之事。”[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448页。]故致曲与“尽性”相对,它不是感通万物之性,进而与天地参,而是将诚运用到具体事物中,通过“形”、“著”、“明”、“动”、“变”、“化”的过程,发用为道德行为,产生道德感化,实际反映的是诚由内而外,自主、自发的实践活动。而《不苟》的“养心”,如上文所说,主要体现在意志对仁义的持守和践行上,故说“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守仁”意近于《解蔽》的“思仁”,仁之所以需要守,是因为仁虽然是内在的,但还需要经过心的自觉,否则会流失、遗忘,所谓“操存舍亡”是也。“行义”的“义”,不应是《王制》的人“且有义”,这种义虽然是人生而具有的,但没有具体内容,只是一种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自然无法践行了。在荀子的思想中,可行之义,只能是社会中的义,是前一种义的具体落实,是义外之义,而非义内之义。故《不苟》虽然受到《中庸》的影响,但对其内容不是简单接受,而是做了一定调整、变化,不仅将致曲变为养心,还在诚的实践过程中加入了仁、义两个概念,提出“唯仁之谓守,唯义之为行”。《中庸》虽然没出现心字,但其诚乃道德主体,接近于道德本心,由诚出发可以由内而外,表现为自主的道德行为,用孟子的话,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而《不苟》的诚,只是养心的功夫和手段,其本身不具有道德创造力,不能直接由内而外发用为道德行为,而是要“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需要经过守仁、行义的环节,“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形,朱熹注:“积中而发外。”[ (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31页。]但《中庸》的“诚则形”是诚积中而发外,而《不苟》“守仁则形”则是仁显现于外,诚只是起到守仁的作用。理,条理。根据义而行,则有秩序、条理。故《不苟》的诚恰恰是“行仁义也”,而不是“由仁义行”,是实践外在的道德规范,而不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发用、自我决断。试做比较:
《中庸》:诚—形—著—明—动—变—化。
《不苟》:诚—守仁—形—神—化;
诚—行义—理—明—变。
《中庸》由“诚”到“化”,一贯而达;《不苟》则分别经“守仁”以达“化”,经“行义”以至“变”,故是仁、义对举,仁是内,义是外,严格说来其思想更接近仁内义外。守仁可达至化,即感化;行义可产生变,即改变。改变易于感化,感化可使变化,仁、义之功交替作用,如天地之运行、四时之有序,故可称为天德。而天地之所以合德,是因为其都是诚的体现。故天不言高而人推其高,地不言厚而人推其厚,四时不言时而人预知其季节。“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夫”,代词,指天地、四时;此,如此;“有常”,即《荀子·天论》的“天行有常”。不过《天论》是从自然义言有常,天是自然天,天行即天道,指自然规则。而《不苟》则从道德义言有常,认为天地、四时有常,正是其至诚的表现。此天是道德天,与《天论》的自然天有所不同;《天论》主要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而《不苟》则吸收了思、孟的思想。天地以诚成其序,人以诚成其治,故君子默然不语就能使民众领会,不施恩惠就能使民众亲近,不用发怒也使民众感到威严,“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夫”,代词,这里指民众;“顺命”,顺君子之命;“慎其独”,慎,诚也;独,指内在的意志、意念,故慎独即诚其意,[ 参见拙文:《朱熹对慎独的“误读”及其在经学诠释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04年3期;又见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292~300页。]这里指诚心守仁、行义。民众之所以如此听命,是因为君子真诚地守仁、行义,做到了慎独。“善之为道也”,“善”指仁、义而言;“不诚则不独”,“独”,动词,训为内。善或者仁、义作为原则,没有诚则不会内在于心,没有内在于心,则不会表现于外,即使起于心意,现于颜色,出于言语,民众也不会信服,即使服从也一定会存疑。正可谓“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对子思、孟子严加指责,斥之为“略法先王而不知统”,而在《不苟》篇中却主动吸收子思、孟子论诚的思想,这个变化耐人寻味,应该反映的是荀子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至于《非十二子》与《不苟》时间的先后,学界则有不同的看法,廖名春主张《不苟》应早于《非十二子》,为荀子前期作品,[ 参见廖名春:《荀子新探》,第56~57页;笔者也曾持这种看法,参见拙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231页。]而张涅则持相反看法,认为《非十二子》为荀子前期作品,而《不苟》为晚期作品。其理由是:1、《非十二子》篇首句称“假今(引者注:犹言‘当今’)之世”,显示出此篇写作时“十二子”应在世,至少仍有很大影响。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前,魏牟、陈仲、宋钘、慎到、田骈、惠施、孟轲都健在。即使过时,影响也尚在,其批判有针对性。而到了荀子晚年,法家起,十二子熄,已无批判的迫切需要了。2、荀子早期热衷于社会政治,到稷下后才成为传经大师。在战国初,传经之事以子夏的贡献最大,但《非十二子》却斥责“子夏氏之贱儒”,而在荀子后学所记的《大略》篇中,却有对子夏的颂扬之语,这应该是荀子从早期到晚期思想变化的反映。3、荀子在稷下综合融通各家学说,建立起以礼治为中心的思想体系。离开稷下到楚地兰陵后,思想有注重心性之学的倾向。兰陵曾为鲁国“次室邑”,荀子在兰陵备受尊敬,可推知其后期思想与鲁学有相合之处。4、《大略》篇多有与强调与外在礼治思想不合,而与思孟之学相近的内容,如“王者先仁而后礼”、“礼以顺人心为本”、“小人不诚于内而求之外”等。另外,“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同于《孟子·梁惠王上》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显然承之于子思的“忠臣”观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而与荀子“隆君师”的观点有明显差异。《大略》从正面记录孟子的事迹,也说明荀子后期对孟学的态度已发生转变。张说是,当从之。[ 张涅:《荀学与思孟后学的关系及其对理学的影响》,《东岳论丛》2003年1期。]可作补充的是,《不苟》与荀子前期作品《富国》《荣辱》的内容明显不同,而与在稷下学宫晚期的《解蔽》篇有一致的地方,都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这也说明《不苟》不可能为荀子前期的作品,而应完成于荀子的晚年,实际代表了荀子的“晚年定论”。
由《不苟》的晚年定论可知,荀子后期出现向思孟之学的回归,不再视后者为水火,而是自觉吸收其思想为己所用,这一变化在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情性、知性的二重结构,开始向情性、知性、仁性的三重结构发展。继《解蔽》的“思仁”之后,《不苟》提出“守仁”,在情性和知性之外,强调了仁在道德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论是思仁,还是守仁,都是意志修,是对意志的塑造和培养,属于治心或养心的内容。不过对于仁是否属于性,仁与心又是什么关系?荀子尚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另外,《不苟》提出“诚心守仁”,而诚又是“君子之所守”,难免叠床架屋,理论上有粗糙、不成熟的地方。其次,从荀子思想的发展看,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主要还是面对仁与礼的关系这一儒学的基本问题。孔子提出仁,以说明内在主体和价值原则,又重视礼,视礼为文明的因循和积累。一方面以仁释礼,以仁的价值重新审视礼,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礼来实现、成就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但对仁、礼关系尚未做出明确说明,故孔子思想中虽然蕴含着情性、知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但还缺乏理论的自觉,还没有从人性的角度对仁、礼关系做出明确说明。孔子之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提出“道始于情”、“礼作于情”,[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37页。]故是以情释礼,此礼主要是礼节、礼仪之礼。孟子则以仁释礼,提出“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恭敬之心,礼也”(《告子上》),但这样以来礼被归于心,所推出的只是礼貌之礼,礼的内涵较之孔子反而大大萎缩了。到了荀子,则以情性说明礼义所以产生的根源,以知性为礼义得以产生的条件,故是以情(欲)释礼,以知释礼,同时又以仁为礼义的内在原则,以仁性为实践礼义的必要保证,故是以情性(欲性)、知性、仁性来释礼,其礼主要是制度之礼、礼义之礼,只是这一工作尚没有真正完成而已。还有,荀子吸收思孟的诚,当然是想通过以诚养心确立道德主体,赋予心一定的道德自主,修正前期思想中过分重视师法、圣王的倾向,但在对诚的理解上又与思孟尤其是孟子有所不同。在荀子那里,诚与心不是合二为一,成为内在道德主体,引发道德行为,而只是养心的手段和方法,以诚养心可以使心持善、知善、行善,但心不可以直接发用为善。故荀子晚年向思孟的回归,并非殊途同归,而是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在吸收、借鉴思孟思想的同时,试图建构不同于思孟、更为完备的人性论学说,只是这一工作并没有真正得以完成而已。从这一点讲,荀子的晚年定论其实也是未定之论,而这一未定之论,则应成为重新思考、检讨乃至重建儒家人性论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课题。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