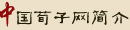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哲学思想
当前页面 / 首页
性恶论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发表时间:【2014/7/21 16:20:43】 浏览次数:11301次
惠吉兴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石家庄050051)
关键词:性恶论,人性论,政治哲学,启蒙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理论主要有三派:即性善论、性恶论和性善恶混论。真正公开主张性恶论的思想家只有荀子。为此,他曾不断受到后人的洁难、批评。从表面上看,主流思想家都对性恶论持否定的立场,但实际上,荀子性恶论的一些基本思 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后人所接受和改造,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性恶论与中国古代人性论的演进
荀子的所谓人性是指天生的自然素质,其内容是人的欲望和本能;人的欲望是产生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人性是与社会道德相对立的。道德(荀子称为“伪”、“文理隆盛”)是对人性教化改造的结果,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性为道德规范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故谓:“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这些思想对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的人性理论有直接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人性论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董仲舒从正面继承发展了荀子的人性论。这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人性的本质问题上,二人都主张人性是人的本质和情欲,这些都是天生的自然资质,与生俱来,不待教化修养。荀子称:“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董仲舒则说:“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螟,情亦性也。”(同上)他以情为性,进一步明确了人性就是人们物质情欲和生理本能,突出了它的“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的自然特征。其次,在善的来源问题上,二人都主张善是圣王后天教化的产物。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人不能停留在本然原始状态,“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董仲舒进一步认为,性是先天的,善是后天的;性是内在的,善是外在的。人性之善有待于后天圣王的教化,“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诲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春秋繁露·实性》)人性之内虽没有善的内容,但却有“善质”,即人性具有向善良转化的资质或基础,善是王教对天然性情改造的结果,“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这句话显然是荀子《礼论》中所谓“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的翻版,两人的思想甚至句式都完全一致。第三,二人都批评、否定了性善论。他们认为,性善论不仅与大量的社会现象不符,而且贬低、否定了圣人的社会作用。所以,两人都明确把孟子的性善论当作批判对象。总之,在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对性善论的批评、对人性与教化的关系等问题上,董仲舒完全接受了荀子的观点。
当然,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不会简单地重复荀子的思想,他也部分接受了孟子的性善论,并以阴阳二气的属性来解释人性善恶的关系。他认为,性生于阳,情生于阴,表现其阳者的即性善,表现其阴者的即性恶。这意味着善恶之性皆为人之所有。他还提出了性三品说,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屑之性。这些不仅修正、发展了荀子的人性论,也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上调和孟荀的先河。循此路术,东汉初年的扬雄公开折衷孟荀,提出了人性为“善恶混”的观点,并将善恶之性与阴阳二气联系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人性论发展的中间环节。
宋明理学被视为先秦儒学的复兴,在人性论上,占支配地位的是孟子的性善论,而荀子的性恶论则以批判的方式被整合,成为理学人性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学家们从理气关系、共相与殊相关系来阐释人性问题,他们认为,人性来源于宇宙本体,这种本体之性纯善无恶,它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由于理气的运动,本体向现象界转化,形成了具体的人性,具体的人性有善有恶,它具有特殊性、偶然性。
张载首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认为天地之性是源于太虚之气的道德仁义,气质之性是太虚之气凝结物化的结果。人的性格、智力、才能和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都属于气质之性,它源于“所禀之气”。气有善恶、正偏、清浊、刚柔、缓速、通塞等属性,人性也就有美恶、智愚、贤不肖之别。
二程认为,天理人性实为同一本体。但人性又不可一概而论,须从天地之性和气享之性两个层面来分疏。他们对传统命题“天命之性”与“生之谓性”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天命之性指“性之理”,生之谓性指“禀受”,即气禀之性,“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天命之性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善性,气禀之性则有善有恶,“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同上,卷一)只有将性理和气禀结合起来,才能讲清人性的善恶问题,“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同上,卷六)
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论。他认为,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既确立了性善的本体地位,又阐明了现实中人性之恶的原因,因此,他称赞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概念“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朱子语类》卷四)。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各种人性论观点,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还是扬雄的善恶混和韩愈的性三品,都不够完善,“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同上)他不赞同孟子将恶之性完全归罪于后天的私欲之累,认为性善论只见到了本体之性,没有涉及气质之性,是不完备的。朱熹主张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结合起来,“所谓天命之与气质,亦相衮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 一,便生物不得。”(同上)这实际上是对孟荀人性论的综合。
从以上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人性论吸收融合了先秦以来的性善论、性恶论以及善恶混等思想成果,理学家们以天地之性作为其人性学说的本体论或逻辑前提,肯定气质之性是人性的现实存在,论证了现实人性的善恶都是气禀所致,具有先天因素。显然,在理学人性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气质之性脱胎于荀子的性恶论。
此外,在改造、转化人之恶性方面,宋明理学也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化性起伪”是荀子人性论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人性虽是天生的,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后天的环境的作用下发生变化,“性也者,吾所不能去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荀子的人性改造论对秦汉以后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很大影响,董仲舒的继善成性说自不待言,宋明理学的变化气质说尤为显著。理学家们看到,气质之性中的先天之恶不可避免,应该也只有依靠后天的努力,改变气质之性,返达天地之性。张载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又说:“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经学理窟·气》)二程说:“惟理可进。除是积学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同荀子的倘使“途之人伏术为学”,则必然由愚而明,由弱而强,何其相似。
宋儒对荀子人性论的接受、改造,前人早有察觉,戴震曾指出:“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荀子之所谓性,即宋儒之所谓气质”,“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孟子字义疏证·绪言》)钱大昕谓:“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跋荀子》,见《荀子集解》考证上)这些论断充分阐明了荀子的性恶论在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古代人性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性恶论,中国古代的人性理论将会是多么苍白单薄。
二、性恶论与中国古代政治哲学
礼法结合的治理模式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的统一体,这种治理模式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它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根植于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们不可能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中发现礼法结合治理模式的历史合理性,他们只能从神启(宗教)、天道(自然)和人性中寻找和建立这种合理性的依据。因此,中国古代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人性论、特别是性恶论便成为礼法治理模式的的理论基础。
第一,性恶论为礼法结合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提供了必要性、合理性。荀子认为,人性中无限膨胀的贪鄙嗜欲必然导致人们为获取有限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而相互残害争斗,结果会造成社会秩序和人类种群的崩溃瓦解,因此,必须建立起社会的权威力量,通过道德和法律规范,限制和改造人的自然欲望和行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荀子写道:“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这句话表明,君权、礼义、法刑之所以必要、合理,就是因为人性偏险悖乱,社会秩序不能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反之,如果人性皆善,人人以仁恩礼让相对待,君王礼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韩非发展了荀子的思想。他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连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也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韩非进而认为,人的自私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无论是齐家还是治国,都不能依靠道德教化,而只能仰仗法刑威慑,他称:“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又说:“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韩非子·奸劫拭臣》)
董仲舒把礼法为代表的社会制度规范看成是社会的堤防,社会的治乱兴衰主要看这堤防能否将那如洪水猛善般的百姓的欲望围困住,他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谊,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圣人、教化、法度是治天下之本,所谓治天下,就是圣人通过教化改造人的本性,通过法度防遏人的情欲。
王充将人类社会规范的产生和存在完全归因于人的性情,他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为作者,情与性也。”(《论衡·本性》)无论是节情防欲,还是通情养欲,礼乐制度都是由性情而生,为性情而作,这就将封建社会规范同人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封建礼法制度和治理模式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性恶论为礼法结合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董仲舒曾说:“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春秋繁露·正贯》)这是说,治国理民必须了解人的本性情欲,否则一切政治原则和措施就会缺乏针对性,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思想家们正是从人性论出发探讨了礼法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何以可能的问题。
荀子认为,好利恶害、好荣恶辱、好富恶贫、好贵恶贱是人的天性,每个人概莫能外,圣王为政之道就在于充分利用人的这一天性,诱之以所好,惩之以所恶。他说:“以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故赏之以富厚,而罚之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荀子·正论》)针对人性好恶而设定的赏庆刑罚对人有极强的诱惑力和驱动力,它能使百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为之奔走竞进而不辞。
荀子的学生韩非片面继承了荀子的思想。他站在法家的立场,否定了礼义道德的作用,主张单纯依靠赏罚来治理国家。赏罚的根据也同样是人性的好恶之心,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性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又说:“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韩非子·制分》)在韩非看来,治民的关键是利用好刑德两手即杀戮和庆赏,这是君主所操执以治事的两种权柄,对百姓要赏其所好,罚其所恶。正因为人有好恶之性,故赏罚之道才得以实行,假如人没有好恶之心、荣辱之欲,统治者也就无法实现对百姓的控制。
对上述思想,董仲舒论述的最为详尽,他写道:“民无所好,君无以权也;民无所恶,君无以畏也。无以权,无以畏,则君无以禁制也。无以禁制,则比肩齐势而无以为贵矣。故圣人之治国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音以诱其耳目,自令清浊昭然殊体,荣辱踔然相驳,以感动其心,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法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劝赏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恶,是以畏法而不得过也。”(《春秋繁露·保位权》)董仲舒深知,只有充分利用人性有所好、有所恶的弱点,设立赏赐、刑罚,才能对百姓加以“禁制”,如果民无好恶,人君也就失去了操纵的把柄。所以,圣人制民,一方面要防欲,使之“不得过节”;另一方面又要致欲,以功名利禄等“诱其耳目”、“感动其心”,使之“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同上)这些足以揭示人性与封建政治的关系:即因为人性恶,所以需要圣王礼法兼治;也正因为人性恶,所以圣王的礼法兼治才能够实现。
三、性恶论与明清早期启蒙哲学
性恶论把人性等同于人的私欲,视私欲为纯粹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是不可改变的天性,在这种意义上,性恶论认可了私欲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对待私欲问题上,与孟子的寡欲不同,荀子主张节欲和养欲。他认为,礼义道德等社会规范的起因和目的就是节制和疏导人们的物质欲望,使欲望能够在合理(礼)的范围内获得满足和实现,换句话说,“给人之欲,养人之求”是礼的基本社会功能,故曰:“礼者,养也。”所以,荀子的理想境界既不是道家的纯任自然,也不是孟子的纯任礼义,而是人的自然天性与社会道德的结合,即“性伪合”。荀子这一以感性欲求为基础的礼欲统一观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批判思潮中获得了充分发展,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一,在“公”“私”关系上,启蒙思想家肯定“私”的正当性、合理性,反对假借“公”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正当权益。李贽公开主张人皆有私的观点,他认为,财货美色、功名利禄,皆人人所好,概莫能免,圣人也是人,不能不穿衣吃饭,“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李贽宣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藏书》卷二十四)在李贽看来,私心物欲不仅是人的天性,自然之理,也是人生的动力,人们奔走竞进皆为“富贵利达”,否认人有私心,既与事实不符,也没有任何益处。
黄宗羲不仅肯定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而且还把它看成是人的权利,“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但进人文明社会以后,专制君主把为众人谋利益的义务转变成为个人谋利益的权力,将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将天下之害尽归于他人,使天下百姓不敢自私,不敢自利,“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同上)在他看来,每个人的私利合起来就是天下的公利,专制君主的主要罪恶恰恰是妨害了每个人的私利的实现,它以牺牲天下公利(每个人的私利)来满足君主个人的私利。
第二,在理欲关系上,启蒙思想家肯定人的物欲的合理性,主张理欲结合,对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
在理学家那里,理欲是完全对立的,“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三)既然如此,要想存养天理,只有铲尽人欲,“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 二)这种蔑视人性的理欲观受到了后人的严厉谴贝。
首先,启蒙思想家们将人欲同人的生命存在连在一起,确立了人欲的不容置疑的价值。陈确赞成人欲是“生机之自然不容己者”这一观点,称这是百世不易之论。他认为,人不能无欲,佛道所主张的清净无欲实际上是无欲之欲,“真无欲者,除是死人。”(《与刘伯绳书》)王夫之认为,人们甘食悦色是“天地之化机”,这是无法禁止的,“断甘食悦色以为禽兽,潦草疏阔,便自矜崖岸,则从古无此苟简径截之君子,而充其类,抑必不婚不宦,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而后可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戴震强调生养之道“存乎欲”,他说:“夫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之资以养者,生道也。”(《孟子字义疏证·绪言》)
肯定人欲与人的生命相始终,也就揭露了理学家灭尽人欲的荒谬性和危害性。陈确指出:“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陈确集》)王夫之说:“乃朱子抑有‘合下连根铲去’之说,则尤愚所深疑。”他指出,这种“连根铲去”正是佛教的禁欲主义,同传统儒学无共同之处,“孔颜之学,见于六经、四书者,大要在存天理,何曾只把这人欲做蛇蝎来治,必要与他一刀两断,千死千休?”(《读四书大全说》卷五)对宋明理学禁欲主文揭露最深刻、批判最猛烈的是戴震,他说,宋儒以来,津津乎理欲之辨,“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理学家所谓的天理,只是一个虚名,实质是禁绝人的情欲;他们所谓的人欲,无非是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喜怒哀乐、男欢女爱这些自然情感和欲望。但是,这些作为自然本能的情欲又如何能灭尽?所以,宋儒的理欲之辨,一方面造成无数欺世盗名之人,祸患天下,“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另一方面,理欲之辨成了尊者、长者、贵者压制、迫害乃至残杀卑者、幼者、贱者的工具,“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同上)“酷史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其次,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欲是天理的前提和基础,天理要通过人欲来体现,它不能脱离人欲而独立自存,没有人欲也就不会有天理。李贽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陈确主张“理在欲中”,“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与刘伯绳书》)没有人欲,也就没有什么天理可言。在陈确看来,理是指合乎人情的生理要求,而欲则是人的生理上不可缺少的机能,从人的自然本能来说,饮食男女和功名富贵是道德和义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饮食男女皆义理所从出,功名富贵即道德之攸归。”(《无欲作圣辨》)王夫之肯定“有欲斯有理”,他说:“礼虽纯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自注:饮食,货;男女,色)。虽居静而为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章其用(自注:饮食变之用,男女合之用)。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人欲是基本的存在,理则是人欲之理,它不仅需要通过人欲来体现,而且只有在饮食男女之中才能实现它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人欲和天理的关系并非是理学家所言的你存我亡、此胜彼退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统一关系。
复次,在理欲统一的前提下,启蒙思想家对人们的物质追求和享乐给予了肯定。王夫之称:“君子敬天地之产而秩其分,重饮食男女之辨而协以其安。苟其食鱼,则以河鲂为美,亦恶得而弗河鲂哉?苟其娶妻,则以齐姜为正,亦恶得而弗齐姜哉?”(《诗广传》卷二)显然,这里针对的是朱熹指斥要求美味为人欲而加以否定的观点。戴震进而认为,礼义道德非但不应禁锢人欲,而且应该保障人欲的实现,真正的道德既能遂己之欲,又能遂人之欲;既能达己之情,又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把满足民情人欲作为道德和王道的标准,为人们的物质追求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以上所述表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树起了个人、自我和感性的旗帜,这些正是近代思潮的主题,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早期启蒙思想家倡导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自私论、情欲自然说和理欲统一观。毫无疑问,这些思想的主要渊源是荀子的性恶论。由此可见性恶论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深刻影响。
作者简介:惠吉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儒家思想与文化。
电话:13613341008
信箱:huijixing1@sina.com
上一条:叔本华与荀子性恶论浅析
下一条: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