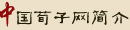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
发表时间:【2014/7/21 16:02:15】 浏览次数:11297次
韩 星
一、治道的概念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出版,提出其“政道”与“治道”说,从“政权”与“治权”二分的角度解析中国传统的治国理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牟宗三先生将政治(权力)分判为“政权”与“治权”,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因此,遂有人说,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吏治相应治道而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所谓政道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政道”,即“政治上相应政权之为形式的实有,定常的实有,而使其真成为一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之‘道’也。”所谓“治权”,即“措施或处理公共事务之运用权也。”[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相应的,所谓“治道”,“就字面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其本质就是‘自上而下’的。无政道的治道,尤其顺治道的本质而一往上遂,故言治道惟是自‘在上者’言。端本澄源,理固应如是。治道之本义只是一句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它表示一种‘智慧之明’。是以在上者涵盖愈广,则治道亦随之而愈广大精微。”[牟宗三:《论中国的治道》,《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至于政道与治道的关系,牟宗三说:“治道者,在第二义制度下措施处理共同事务之‘运用之道’也。政道是一架子,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故是一‘理性之体’,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故是一‘智慧之明’。”[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这即是说,政道与治道构成一种本末体用的关系,前者派生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运用,而此二者则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外在分离的关系。牟先生对“政权”与“治权”、“政道”与“治道”、“政治”与“吏治”的分疏就现代学术体系而言可以说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则未必符合若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治道”是一个复杂而自成体系的概念,“既包括‘治之道’,又包括‘治之具’;既包括‘治之本’,又包括‘治之事’;既包括思想原则,又包括制度措施;或者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既包括政权成立之道理,又包括政权运用之道理。”[黎红雷:《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总序》,第1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先秦诸子中已经把“治道”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来使用,最早如《墨子·兼爱中》云:“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也。”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称作“圣王之法”,亦即“天下之治道” 。《荀子·正论》篇称:“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葬,……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盗也,必以有为,不以备不足,(足)则以重有余也。而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当厚优犹(不)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故盗不窃,贼不刺。”“抇”是指盗墓,当时社会上对盗墓有流行的说法,说是古代没有人盗墓是因为普遍实行薄葬,而后世盗墓猖獗是由于人们厚葬引起的,荀子认为这是不懂得“治道”的说法,然后他进行了解释。《韩非子·八经》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诡使》又有:“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在这里,韩非在圣人如何“治理天下”的意义上使用了“治道”一词,其指涉内容不仅包括赏罚、禁令、利、威、名等为治手段,提及“必因人情”的人性论依据。《吕氏春秋·知度》则称:“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这里推论了除奸、治官、性命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这些因素对于治道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秦汉以降,“治道”一词则得到了更为普遍的使用。秦始皇在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汉初儒者陆贾《新语·明诫》:“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应于上。”治黄老道家之学的胶西盖公称:“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汉书·贾谊传》载贾谊《陈政事疏》:“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汉书·文帝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汉武帝时博士公孙弘上疏自称:“愚心晓然见治道之所以然也。”《汉书·宣帝纪》载宣帝神爵三年八月诏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翼奉传》载汉元帝时东海人翼奉称:“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汉书·礼乐志》载:“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这样看来,“治道”一词已为先秦诸子普遍采用,秦汉以来更为从帝王到朝野士人们所广泛使用。
今天看来,所谓“治道”的义蕴涉及为治的价值指导原则、认知判断标准、人性论依据、天人关系论、无为论、教化论、君主修养论、官吏的任用与考察原则、行政的控制幅度原则等治理国家活动中的各个方面,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治道”,其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治道”广义上的理解。《庄子?天道篇》:“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刑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依据《庄子》的分判,我们说“治之具”作为方法、工具、器物、制度,是“治”(管理)的质料因,它的性质是“有用”,对“治之具”的研究所寻求的是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有效性的改善,是研究效率的问题,因而是科学的。“治之道”则是对此方法、工具、器物、制度的取舍评判的标准它所关切的是人类的文化价值理想,所以是哲学的,作为“治”的形式因,大体相当于“治之理”,可谓狭义的“治道”。事实上,就“治”的实现而言,“治之具”与“治之道”则不可须臾离,因此,从逻辑上说,应当具有一个“共名”来统摄此二者,由此考察二者的关系问题才成为可能,这个概念同样可以说是广义上说的“治道”。[ 程宇宏:《试论“治道”与中国管理哲学》,《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简单地说,广义的“治道”即治国的思想原则,也包括“治之具”即治国的制度措施。在“治之道”方面一般的原则有:天下为公、民本、人治、无为而治等,具体的模式有道家的“道治”、“天治”;儒家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法家的“势治”、“法治”、“术治”;儒法兼综的“礼法兼用”、“德法并行”、“人法兼资”等。在“治之具”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体制有权力架构、职能分工、权力制衡以及吏治方面、经济方面、军事方面、法律方面、文化方面的制度措施。[ 黎红雷:《中国传统治道研究丛书·总序》,第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在我看来,“治之道”属于政治哲学,而“治之具”属于制度建构,前者是是体,是本,后者是用,是末。本文对于荀子治道的探讨,可能既涉及到“治之道”方面,又涉及到“治之具”方面,但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阐述。
二、治道的源流
关于传统治道的模式,近代以来学者们有不尽相同的概括,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把传统治道概括为道家的“无治主义”, 儒家为“人治主义”(或“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墨家为“新天治主义”,法家为“法治主义”(或“物治主义”),并把它与“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区分。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把传统的治道分成三个系统: 一是儒家的德化的治道﹐二是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三是法家的物化的治道。其实,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治道模式的历史演变是有一个清晰的表述的,兹摘引部分资料于下:
《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
《商君书·修权》:“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
《礼记·乐记》:“五帝殊时,不相颂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吕氏春秋·先己》:“五帝先道而后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后事,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后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孔丛子·论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上见尧舜之德,下见三王之义。”
《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颛顼。’孔子曰:‘五帝用说,三王有度,五帝久远故用说也,三王迩则有成法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
桓谭《新论·王霸》:“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霸)以权智。”[《意林》引《新论》云:“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
阮籍《通老论》:“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
黄石公《三略》:“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行焉。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设矩备衰,有察之政,甲兵之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
概括以上材料的意思大致是说,上古时代的三皇,是以道治天下,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也就是说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无所谓权力,不存在政教,天下自然太平,这是最高的境界。到了五帝的时代,以德来治天下,这已经差了一层,已经是有为而治了,但是仍然是相当高超的政治。再往下到了三王时代,仁义之类的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权谋智术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可以说是每下愈况。所谓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三代。
北宋邵雍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化分为四个阶段:皇、帝、王、伯(霸),认为世运的转变是每况愈下,且是循环变化的,并在《皇极经世书·观物篇》概括了人类以来四个阶段的治道模式: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力(法)治国。他说:
三皇同意而异化,五帝同言而异教,三王同象而异劝,五伯同数而异率。同意而异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固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唯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
三皇同仁而异教化,五帝同礼而异教,三王同义而异劝,五伯同智而异率。同礼而异皆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归之,故尚让。夫尚让也者,先人后己之谓也。以天下授人而不为轻,若素无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无素有者,谓不己无己有之也。若己无己有,则举一毛以取与于人,犹有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唯五帝乎?是故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
三皇同性而异化,五帝同情而异教,三王同形而异劝,五伯同体而异率。同形而异劝者必以功。以功劝民者,民亦以功归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谓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贼,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归焉。…
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劝,五伯同术而异率。同术而异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归之,故尚争。夫争也者,争夫利者也。取与利不以义,然后谓之争。小争交以言,大争交以兵。争夫强者也,犹借夫名也者,谓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称也。利也者,养人成务之具也。名不以仁,无以守业。利不以义,无以居功。名不以功居,利不以业守,则乱矣,民所以必争之也。五伯者,借虚名以争实利者也。帝不足则王,王不足则伯,伯又不足则夷狄矣。若然则五伯不谓无功于中国,语其王则未也。过夷狄则远矣。周之东迁,文武之功德于是乎尽矣。犹能维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绝如线,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由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归焉。……
三皇时代以道化民,道法自然,自然的本质即无为,人民于是以道归化,天下由此大治。五帝以德教民,崇尚礼让,礼让的本质是天下为公,人民于是以德归化,天下也可以治理。三王以功劝民,注重政治,政者,正也,王者,正也,以功正天下之不正,人民于是以功归之,可以有天下。五伯以力率民,借虚名以争实利,然中原华夏不为夷狄化者,五伯之力也,人民于是以力归之,可以存天下。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力治国。邵雍还说:“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皇极经世书·观物篇》)他把“皇帝王霸”之说与“道德功力”之说统一并且融为一体了。
三、荀子——先秦治道的集大成者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结束时一位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先秦诸子乃至古代的文化进行批判继承而集大成的人物。郭沫若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批判》第21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侯外庐也说:“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的代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53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徐复观说:“从学术方面说,他承孟子之后,为儒家开创期之殿军,儒家的人文精神,由他而更得到一明确的形态,形成人文精神骨干的礼、乐及由礼而来的‘正名’,孔子只提出一个端绪,在他的都有详尽的发挥。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可以说是儒学的完成者。”[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第2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荀子涉猎广泛,学说渊博,兼综儒道墨法名,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秦汉,乃至其后二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深巨。这与他在稷下呆过有直接关系。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熟悉稷下各家之学,也有了百家争鸣,学术交融的思想自由的宝贵经历,这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思想、构建自己庞大思想体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先秦诸子百家,竞起争鸣,提出了各种学说,他们基本的理论特征是都注重论证“治道”。对此,司马迁说的明白:“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近人也论述道:“周秦之际,士之治方术者多矣。百家之学,众持异说,各有所出,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阴阳、儒、法、刑名、兵、农之于治道,辟犹橑之于盖,辐之于轮也。”[ 刘文典:《吕氏春秋集释·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张舜徽说:“周秦诸子之言,起于救时之急,百家异趣,皆务为治。”[ 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诸子百家见解各异,但其立论的归宿都在论证“治道”。不仅如此,诸子还热衷于政治实践,他们都热切地企盼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其人生理想、学术归旨,目标都指向了政治实践。
李泽厚指出:“从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家’,都一贯抨击荀子,表彰孟子,并以朱熹王阳明直接孟子,认为这才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中国思想史的主流正宗。而三十年来国内的研究则又大都只赞扬表彰荀的唯物论,或则抨击他的尊君尚礼的法家倾向。这些似乎都没有抓住荀的要害。”[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荀子的思想主体是讨论治道,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我们常常说的哲学、经济、法律、教育、伦理思想,都是为其治道服务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或从不同方面说明和论证治道。他从天人关系、大道自然等较高的理论层次构建治道的形而上基础。他从人性论、从人能群等人性和人的社会属性方面论证礼乐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整合功能,形成了集大成性质的礼学体系。进一步,他讨论了王道、霸道、王制、富国、君道、臣道等社会理想,社会治理模式、经济政策、君臣之道等的行为准则以及与君主制度相联系的管理、实施权力等具体道术。下面,就从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梳理。
(一)人道政治——荀子的治道总论
《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有的一系列特点以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是说儒家把道看成是其最高的追求。孔子心目中的“道”就是这样一个最高本体,但孔子谈到道时都是与具体的人生和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在孔子那里,天道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主导的还是人道思想。如他谈人格修养过程,认为作为一个人应该认识“道”、追求“道”、献身于“道”,而且他还断定:“道”是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不遵循的。他说:“谁年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即是说“这个道”就向人们进出的门户一样,是天下众人所共同经由、所共同遵守的。他说:“吾道一以贯之。”(《里仁》)这“一以贯之”的“道”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的忠恕之道,也即是孔子“仁”学的核心。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这段话显然是孔子考察了历史和现实而得出的结论。要复兴礼乐,他认为不能光讲礼乐本身,还要追溯礼乐背后的“道”——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社会理想、政治理念。孔子的“道”自然是承继春秋以来中国文化由天道转到人道的这一历史趋势而进一步探讨的,其传统资源主要是礼乐文化,其价值指向基本上是人文精神,其最后的归宿大体上是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在就使他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意蕴。总论孔子屡屡言及的“道”,其内涵可以包括道德品质、合理行为、正当方式、伦理规范、清明政治、学说主张、真理方法以及技艺、道路等等。
孟子所讲的“道”是贯通天地人“天人合一”的。他在孔子天人观念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只要尽量地扩充人生来就具有的善心,就能认识人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而一旦认识了人自己的本性,就是认识了天的本性,所以,人即天,天即人,天人于是可以合而为一。这样,他对人生和社会政治的设计就有了根本的立足点。孟子以“诚”沟通天道和人道:“诚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道”区分人与禽兽:“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由于社会变化的缘故,孟子更挺立起了士人的独立人格。他说:“道在尔而求诸远”(《孟子·离娄上》),希望士人有高远的追求,“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在坚守道和具体利益之间的权衡上,他强调“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
荀子在天人关系上与孔孟不同的是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他吸收道家天道自然说,提出了“自然之天”,认为天看起来好象复杂而神奇,其实是无意志、无目的的,但它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变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不能任意降人以吉凶祸福,天道不能干预人事,人类社会的治乱只能从社会自身去寻找。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所以,天与人是相分的。明于天人之分目的是要人们不要迷信“天”,应该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控制、改造、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所以他又进一步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关于“道”, 荀子视道为世界的根本原理,具有实体的意蕴。他说:“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不穷,辨乎万物之情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又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荀子·天论》)可见,荀子关于道的理解,是作为物质的自然范畴而把握的,而不曾像庄子那样以“道”为观念的实体。[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第232-23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这样,荀子的“道”与孟子的高远与超越相比,就显得具体、实际多了,甚至有更多现实功利的考虑。如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道也者,治之经理也。”(《荀子·正名》)可以看出,从孔子文化关怀到荀子政治参与的明显变化,显示了孔孟与荀子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孔孟与荀子虽然共同言“道”,但其内涵已经有明显的不同,孔孟的“道”中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批判因素,而荀子则更看重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效果。[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其实,荀子一定程度上还是坚持了原始儒家以道抗政的思想,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荀子·子道》)认为“从道不从君”是儒道中的大行。因为道的存亡决定国家的存亡,“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所以要以道的价值理想作为士人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权势和利益。他希望儒者能够做到“君子立志如穷,虽天子三公问正(政),以是非对。”(《荀子·大略》)这体现了儒家道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君、道二元对立的政治格局。荀子还把这种“道统”与“政统”的分立具体化为“圣”与“王”的并立:“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圣”是人伦道德的承担者,“王”是政治制度的奠定者;只有二者合作,才能治理好天下。显然,这种“合作”是一种理想,而他就以这理想作为天下的最高标准。这样,不但“圣”和“王”之间构成了张力,理想与现实也形成了紧张。
当然,荀子在坚守儒家道义理想的前提下也不得不现实一些,因为毕竟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所以在荀子那里就开始为君子提 出了实际的可操作的“为臣”之道:“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荀子·臣道》)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臣道”,虽然是在为君的前提下,但也不是绝对的被动。不过,应该看到,在荀子这里,臣的地位开始降低,儒家之“道”有“术”化的趋向,即在价值理想与现实存在的矛盾中,荀子不得不放弃某些理想,以适应社会现实,开始了价值理想工具化的历程——秦汉一些儒者就是沿着荀子的理路前进的。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道、圣人和“经典”应该是统一的。他强调:“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荀子·儒效》)“《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荀子之论治道与孔孟一样,也是从历史上进行经验总结和归纳的。学术界一般把荀子的历史思想概括为“法后王”,使之与孟子的“法先王”相对立。其实,荀子不但提出与孔孟接近的“法后王”的观点,也提出了“法先王”的观点,是先王后王并重。统计《荀子》一书,称“后王”的有12处,称“先王”的有14处。“先王”观念的形成以历史上的圣王为摹本,凝聚了古代历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是在理想意义上而不是在现实意义上表述的,这是理解荀子“法先王”的关键所在。他说:“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荀子·礼论》可见,他认为先王之道以礼乐为盛,体现了礼义道德的精神,这与孔子对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的推崇相当一致。因此,人们必须效法先王,因为先王能“审礼”、“隆礼义”、“比中而行”而成就“立文”之道。在荀子的历史观念中,是否法先王是评价一个人道德境界高低的尺度。荀子把那些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言论概斥为“奸言”、“奸心”。他说:“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辨,君子不听(《荀子·非相》),还说:“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荀子·非十二子》)。他批评名家学派惠施、邓析理论的最大缺陷就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荀子还对“略法先王”的俗儒提出尖锐批判,并指出孟子就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荀子·非十二子》)的俗儒。荀子构想了一个历史活动的发动者,超越众生之上的理想人格——先王,以制礼作乐,启蒙民智。荀子法先王,是以对传统历史的眷恋为其心理特征的,在这点上,荀子与孔孟并没有太大差别。
对荀子力量来说,他更重视经验主义,可效法的圣王必须要有确实的事迹,是可据可征的才行,于是他采取了由近及远的历史观,强调“法后王”。荀子之所以要法后王,《非相篇》有过解释:“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同篇又说:“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大略篇》中说:“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以定法度,制礼乐而传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异于变易牙之和,更师旷之律?无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国不待死。”这就明确指出把能不能效法和遵循三代的礼乐法度看成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同篇中又说:“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礼,节也,故成。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虚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把仁义与礼(乐)结合起来,以实现圆满的治道。对于“法后王”,学术界尽管一直有争论[对荀子“法后王”历来就有也有不同的认识,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使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我以为荀子所谓“后王”实即周,“法后王”具体的指的就是法周,这代表了荀子对于西周礼乐制度的肯定。冯友兰说:“在孟子时,文王、周公尚可谓为先王,‘周道’尚可谓‘先王之法’。至荀子时,则文王、周公只可谓后王,‘周道’只可谓为后王之法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354页,中华书局1984年。]因此,荀子的“法后王”与“法先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与孔孟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了。
荀子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国家的君主指出的最理想的治道是“以一持万”的“无为而治”。 《荀子·儒效》:“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以一持万”的前提是“以一知万”和“以一行万”。《荀子·非相》:“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此类行杂,以一行万……故丧祭、朝聘、师旅一也。贵贱、杀生、与夺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可知“以一知万”是由礼推演出来的,在荀子看来,礼由“分”而“类”,因“类”而“统”,由“统”而“一”。这样类推下来就可以“以一知万”。在“以一知万”的基础上,“以一行万”,实现社会伦理秩序统合如一,最后“以一持万”,“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荀子·不苟》)最高的政治境界就是“至道大形……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胑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荀子·君道》)显然,这里荀子所讲的就是“无为而治”的统治术。一般认为,这里的“无为而治”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徐复观认为这是儒家治道的应有之义。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就可以归结到“无为而治”,也就是说,道家有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有儒家的“无为而治”。儒家“无为”的“基底”,是作为人文世界根本的仁,而道家则系自然世界的自然。两家只在这种地方分枝,但在要求人君“无为”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99、30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其实,《论语·卫灵公》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物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已经通过大舜的政治行为方式,明确地提出了无为而治的观点。
这种“无为而治”的治道荀子还以“垂衣裳”进行了象征性表达。在《荀子·王霸篇》中他说:“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舜。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在此,荀子以尧、舜为实践“垂衣裳而治”的典型,认为“治国有道”就是“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荀子·王霸篇》又载:“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这里的“垂衣裳而天下定”同上面所谈到的“垂衣裳而天下治”,无论是“定”还是“治”,实际上都是指“无为而治”的治道。
(二)隆礼重法——荀子的礼法合治
礼在古代有多重含义,礼貌之礼、仪节之礼、伦常制度之礼,从春秋以来就有这样的区分。礼治、礼法、礼俗、礼教、礼律从不同层次表述礼的内容和功能。礼治是从殷商带有浓重神权色彩的礼乐传统中脱胎出来的,它更注重人事、重民,故又有“德”与之配合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主体。礼治在春秋礼崩乐坏之时发展成为“礼治思潮”,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在理论上对礼治进行了加工和深入探讨、广泛宣传,使得当时无论是改革家,还是保守派,都接受了这种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政治主张、措施,不论是创新的、守旧的,都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形成[徐进:《礼治的精义及其影响》,《文史哲》,1997年第1期。]。
至于“法”,从现有青铜铭文资料与古文献所载相印证,可以肯定春秋以前的“法”字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字无关。可以说,西周时期人们只知“刑”而不知“法”,甚至春秋时人们还不懂得“法”的意义。如《左传》所载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叔向写信反对。子产所公布的法律当时称“刑书”、“辟”,而不称为“法”。后来晋铸刑鼎,孔子进行批评,虽然谈到了“法”字,但这里的所谓“法”、“法度”并不是今天常说的“法”,而是指礼制。“法”字在文献中大量出现是在战国时期,如晋有“被庐之法”,楚有“茅门之法”,魏李悝撰次诸国法,作《法经》。这样,法的观念就伴随战国蓬勃发展的成文法运动诞生了。与此同时,在战国变法运动中,以法的观念为核心形成了法家学派,他们大讲“更法”、“变法”、“以法治国”等,把“法”的观念发展为法家思想体系。
战国时代儒家主要崇奉礼治,与当时“缘法而治”的法家展开了争辩,儒法之间在礼治与法治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一度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但是如果辨证地看,儒法之间实际上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整体对立,而是相互沟通,具有同一性,有许多重迭之处。儒家也讲法,法家也讲礼。儒家反对法治、任刑,主张礼乐教化,但也决没有摒弃刑法之意。[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第234-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
事实上,在中国思想史上,礼与法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具有很强的互补作用。如果不是从表面而是从实质来看,我国古代讲法必讲礼,讲礼也必讲法,二者好象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离。法与礼共同作为行为规范,既有分 司分治的一面,又有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另一面。凡礼所不容的,必为法所禁止;凡礼所不禁的,法亦不禁。违礼即违法,违法亦违礼。胡适论礼与法的区别云:
礼是“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所以为民坊”,这都含有政治法律的性质。大概古代社会把习惯风俗看作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故“礼”字广义颇含有法律的性质。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其中却有一些分别。第一,礼偏重积极的规矩,法篇重消极的禁制;礼教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法教人什么事是不许做的,做了是要受罚的。第二,违法的有刑罚的处分,违礼的至多不过受“君子”的讥评,社会的笑骂,却不受刑罚的处分。第三,礼与法施行的区域不同。《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为上级社会设的,法是为下等社会设的。礼与法虽有这三种区别,但根本上同为个人社会一切行为的裁制力。[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96页,中华书局,1991年。]
正因为这样,在战国末期出现了统一趋势的情况下,荀子一方面继承、发展和修正了儒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继承、发展和修正了法家的“法治”,并在新的封建基础上以“礼”为主,使礼、法统一起来,形成了“隆礼重法”的思想。这一思想使他能够既适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又顺应思想学术的演变逻辑,使礼与法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的治道模式。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是有学术渊源的。其远源就是孔子。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汪中:《荀卿子通论》,《述学》第77页,戴庆玉等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孔子以西周为自己政治要恢复“礼治”,即“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是因为,西周以来,特别是春秋之际,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也就是一种“无道”即“王道”失落的表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可见,孔子所谓“有道”,就是欲恢复由“王”来行“礼乐征伐”之权的“道”,也就是礼治。欲使礼治复兴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还必须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孔子认为必须从“正名”开始。子路问孔子:“卫君侍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而所谓“正名”,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礼乐制度的恢复,使社会处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样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也就是要使封建宗法制中的各等级各安其位,各享其权,各尽其义,不能彼此僭越,否则,诚如齐景公所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认为,只要能够做到守礼,所谓“犯上作乱”之事也就不会发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又说,“上好礼,则民莫不敢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荀子继承和改造了孔子的礼治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礼法合治观。
其近源是稷下学宫礼法融合的学术思潮。礼法结合是稷下学术的一个普遍特点,这种政治理论在稷下不断丰富和深化,为荀子进行理论总结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荀子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使礼治与法治的结合更加紧密,使这种政治模式理论臻于完善。不同的是,稷下学者们结合礼法都具有以法治为主而以礼治为辅的倾向;荀子则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来吸收法治的思想,提出了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政治模式理论。[白奚:《稷下学研究》第281页,三联书店,1998年。]
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注重规范和制度,非常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儒家礼治的思想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国之命在礼”(《荀子·天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是治国的根本和最高准则,所以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荀子·礼论》)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
与此同时,荀子还吸收了前期法家的理论成果,援法入礼,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两者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交融互摄。为此,他认为礼是法的纲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礼之大枢要”。(《荀子·王制》)故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至道之大形,隆礼重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他有时对礼的界定实质就是法,如说:“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王霸》)这就使礼具备了严谨性、外律性、强制性。荀子强调礼与法的一致性,并进一步提出了“礼法”的范畴:“故学也者,礼法也。”(《荀子·修身》)“立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荀子·王霸》)荀子的做法与孔孟显然有离异,故学界多有批评,吕思勉说:荀子“专明礼,而精神颇近法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84页,东方出版社中心1996年。]蒙文通说:“孔孟之道……荀子以法家乱之而滞于实。”[蒙文通:《儒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古学甄微》第67页,巴蜀书社1987年。]这些论说尽管很有道理的,但是应该考虑到时代变了,荀子援礼入法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拓展儒家的思想领域。对此,任继愈就持肯定态度:“这样用法治来充实改造礼治,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荀子对于礼、法,或分说之,或合言之。合言之则曰“礼法”;分说之,则以“礼”为“治之始”、“法”为“治之端”,这说明荀子仍然未与法家完全合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197-1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荀子援法入礼,正是看准了强制性的法可以为礼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他并没有背离儒家的基本精神。肖公权说:“荀子之政治思想以法为末,以人为本。故近申商者其皮毛,而符合孔孟者其神髓也。”[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10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但是,荀子的援礼入法毕竟对法家还是产生了重大影响。陈柱曾说:“法家盖起于礼。礼不足为治,而后有法。礼流而为法,故礼家流为法家,故荀卿之门人李斯、韩非皆流而为法家也。”[陈柱《诸子概论》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则知韩非“法”的思想曾有荀子“礼”的思想的影响。
荀子认为礼与法并非是互相排斥的,二者的施用本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是可以互补的,应该联手并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治国效果。他主张礼法并用:“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这里是以性恶论作为其礼法并用的理论基础的,体现了综合治理的思想。他又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 荀子的礼法并称,实际上是以礼兼容了法,使法有了伦理化倾向,与礼的性质极为接近。《荀子·修身》云:“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这说明,荀子的礼法并称带有以礼化法的意思。
荀子的礼法并用是有区别和侧重的,礼法实质上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层面。从礼的角度看,礼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哲学(政治原理、原则),法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制度;从法的角度看,礼类似于今天的宪法(根本大法),法类似于今天的各项具体法律规范。因此,二者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荀子·富国》)治国“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荀子·富国》) “用刑政治百姓,备礼义待君子。”(《荀子·致士》)因此,他认为礼之用为上,法之用次之。他认为礼比法更根本,“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故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修身》)他是主张治道应该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
(三)德主刑辅——荀子的德刑兼用
无论从过去的文献还是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很多关于“德”的记载,说明周人非常重视“德”,大力宣扬“德”思想,也说明周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是“德治”并与“礼治”相配合。这一思想后来为儒家学派继承和发展,演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与礼治密切相关的德治思想传统,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我们一般把注重统治者的个人品行及依靠道德教化实施统治的为政方策称为德治。
近代以来,在学界,首先是梁启超提出儒家政治法律思想是“德治主义”,但他又把“德治主义”与“人治主义”和“礼治主义”看成一回事,这似乎欠妥。对此,瞿同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儒家既坚信人心的善恶是决定于教化的,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其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德治主义又衍而为人治主义。所谓德治是指德化的程序而言,所谓人治则偏重于德化者本身而言,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张中秋:《中国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樊浩:《人治与法治比较——中西法律精神的比较》,《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今天,有的学者以人治概括中国古代法的根本精神,并认为人治的核心是礼治,而另一重要内涵是德治[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第1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也就是说,人治可以包涵礼治、德治等。
法与刑可以转注,在春秋以前人们只知有刑,不知有法。三代及以前,法就是刑,或者更准确地说,早期的“法”是以“刑”为中心的,早期的“礼”又具有今天所谓的“法”的功能,所以,早期政治文化传统中只有礼和刑(后来才有德,再后来又有法)两个概念。商周时代有“型”字即后来通行的“刑”字的原字,后来的刑字除了主要表示刑罚意思外,还有杀戮、征伐、模范(又引伸出规范、法)、刑正、取法、形成(又引伸为形式)、恒常等意思。从刑字的产生、演变,反映出商周时期人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深化。
孔子的治道主张是重德轻刑。
关于“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政和刑,是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德和礼,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朱熹注云,“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认为“刑”、“政”是实现“治”的辅助方式,而“德”、“礼”则是实现“治”的根本的,而“德”又是根本的根本。孔子所言政、刑、德、礼几个概念,被后儒逐渐概括为礼乐刑政一整套治道的观念系统。相近的说法见于《论语·里仁》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里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说他们念念不忘德与刑,分明是主张德刑并用,以德为主是治国之上策。《孔子家语·刑政》引孔子话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礼记·乐记》中强调:“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乐大体不相当于今天说的德治,刑政大体相当于今天说的法治或者政治文明,这是古代中国人对法治与德治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知识。礼刑政四者目的是一政的——“同民心而治道”;四都到位并且不相互冲突,治道就完备了。这也就是说,古代“治道”主要包含了礼、乐、刑、政四个方面。王国维先生对此也有阐述:“礼乐用陶冶人心,而政刑则以法制禁令刑罚治民。前者为道德,在修人心;后者为政法,在律人身。虽此二者相合,然后成为政治,但其所最重者,则在礼乐。”[《王国维文集》第15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孔子还把德、刑作为宽、猛两种统治手段,认为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交替使用。政治上宽猛相济指的就是政治措施要宽和严互相补充,刚和柔相反相成。《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郑国执政子产死后,“子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于是子大叔出兵镇压,“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对此,孔子评论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可见,孔子意识到:虽然“宽则得众”,但是,政宽也有它的缺点,“道之以德”也有它在功能上的不足,这就是“政宽则慢”。“慢”者,轻慢也,故必须“纠之以猛”。这样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德刑并用,才能有和谐的政治。
孟子提出“仁政”主张,强调“以善养人”、“以德服人”,他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能 服大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并且举例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可见,他的“仁政”是要通过“以善养人”,使老百姓心服。怎么才能做到呢?他举舜的事例说明统治者应该像大舜那样,先有仁义之德,再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教化(养)老百姓,使他们心服,而不是首先要求老百姓如何如何,这样,“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如果“君心不正”,那就有赖于“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孟子强调统治者的道德人格对老百姓的感化,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处,注重普遍人性和内在的道德觉悟,这是其长。但是,相对而言,孟子对外在的礼乐教化以及刑罚有所忽视,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荀子感到了孟子专恃德治的严重缺陷,认为对有些人,象尧的儿子朱丹、舜的弟弟象就只能“待之以刑”(《荀子·王制》),对民应“严刑以戒其心”(《荀子·富国》)。同时,在《议兵》篇中,他又明确否定了以庆赏刑罚为主要治国手段的主张。他告诫统治者说:“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因此,必须将赏庆刑罚与礼义道德结合起来,恩威兼施。荀子继续说:
故厚德享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养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然后百姓晓然皆知循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
这就是荀子为统治者设计的治国方法和原则,一方面统治者要向百姓宣明礼义刑法,“厚德音以先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意在提高老百姓达到道德自律能力。另一方面,统治者也要率先垂范,“时其事……风俗以一”,这之后,如果还有背离风俗,不顺政令、忤逆长上的歼民,便可绳之以法,大刑伺候。这样,就展示了德刑关系的构架: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荀子也继承了孔子“先教后诛”的思想。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这是说实行礼义道德的教化尽管短期内难见成效,但时间久了,就会克服残暴,免除刑杀。他还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故也,况为政者夺其贤者而与其不贤者,以化民乎?知审此二者,则上盗息。”(《孔丛子·刑论》)他极力反对不教而杀,并将其列为“四恶”之首。“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要重视刑罚的作用,但他也认为通过礼义教化是可以改恶向善的。因此,他特别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坚持反对不教而诛和教而不诛的两种偏向。他说:“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因而,他主张先教后诛,先礼后法。
荀子虽然认为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是必要的,但他也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 ”的传统思想,坚持主张实行罪与刑相等的原则,特别反对滥施酷刑的惩办主义。荀子主张,治国理政,临事接民,应有功必赏,有最必罚,“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王制》),“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荀子·议兵》)荀子把公平看作在司法的重要原则:“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荀子·王制》)所谓“公平”、“中和”,就是宽猛相当的意思;既不应罪重而刑轻,也不应罪轻而刑重。他说:“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夫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荀子·正论》)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恶除暴,以儆效尤,如果杀人不用偿命,伤人不受惩罚,无疑于是纵容暴行,宽宥罪犯,这样做,就失去了刑法的本来意义,也威胁到国家的治乱安危。他还举例说,上古治世就不是这个样子,从前武王伐纣,最后砍下纣王的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如此惩暴诛悍,才是“治之盛也”。
(四)粹王驳霸——荀子的王霸并用
王道,亦称王政、王术,即以德礼仁义治国理民之道。《尚书·洪范》首先论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首次揭示王道的基本特征。由于对《洪范》创作的时代有争议,一般多认为可作为殷周之际的史料。即使为春秋战国及其以后人所作,也一定是后人对三代王道的特征的一种概括和理想化。《尚书·大禹谟》也揭示了王道的精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句还见于《荀子·解蔽篇》:“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说明这一思想有很古老的渊源,至今难考。道经或是书名,或是大道之常经的意思。现代学者多云《大禹谟》为伪作,即是如此,这一观念也应是三代就有的,绝非后人造作。]这一点对宋儒影响甚巨,相继信奉并阐发之。按照《荀子·王制》的说法,王道政治包括“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和“王者之法”,王道依靠这些来推行。“霸道”与王道相对,其内涵是以法术刑名治国,霸道的基本特征是“以力假仁”。荀子在论及霸道时说它“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而是靠“乡方略,审劳佚,谨蓄积,修战备,齿刍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荀子·王霸》)就是说它以利害相制、以强力相求,近于强权政治,不同于儒家所主张的王道在于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儒家信奉王道,反对霸道,孟荀更好作王霸之辨。王概念提出比霸早。关于“霸”字,据近人罗根泽考证,王始于周,霸始于春秋,《诗》《书》《易》《仪礼》《春秋》并霸字而无之,至《论语·宪问》始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自后《左传》遂屡见霸字,而伯亦有训霸者矣。但这时的“霸”乃就形势言,非就政治言,言势为诸侯之长而成霸者,非言行如何之政而为霸政。霸为制度名词而非政治名词。至于王霸以政治分别,已到了战国初。王霸之分,就形势言,王者兼有天下,霸者仅为诸侯之长;就政治言,则王植基于仁,霸植基于力。王虽甚古,而必待霸之产生,始因对待而生出不同之政论。[罗根泽:《古代政治学中的“皇”、“帝”、“王”、“霸”》,见《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童书业作过类似的解释[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泽华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王、霸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提出来了,其后孔、墨也都使用过王、霸概念。在孟子之前,王与霸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王指统一的君王,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王与霸都是被肯定的,没有政治路线的含义。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把王与霸作为不同的政治路线概念而使用的是孟子。[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85—8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在孟子这里,“王道”与“霸道”、在“德治”与“力治”两极的对立性被十分鲜明地摆出来了。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尽心上》)
在此,选择“力”,还是选择“德”,就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标——“霸”与“王”。特别是,“用武力征服”,还是“用道德感化”,在庶民那里,还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对孟子来说,理想的选择当然是“王”和“德”。由上文可以看出,孟子分辩王道、霸道是有其特定内涵的,这就是“德”与“力”。因此,王霸之辩实质上又是德力之辩。这样,孟子将霸、王作为两条对比鲜明的治道方略和统一天下的途径提了出来。
在强调王霸对立的前提下,孟子鲜明地表达了“尊王贱霸”的立场。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称霸的事迹时,孟子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意识里,从“三王”到“五霸”,到他所目睹的诸侯和大夫,这既是“力”和“霸”无限膨胀的过程,也是历史严重退化的象征,《孟子·告子》载:“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历史完全是一个从德到力的退化过程。对王霸观念的历史演变,嵇文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王与霸本来不是两种治法,两种主义,而只是地位上的区别。王即天子,霸即伯,指诸侯之长说。春秋时代,只讲霸诸侯,不讲王天下。孔子对于霸者并没有菲薄的意思,他也并没有标榜出与霸道对立的王道。到孟子就不然了。他一方面为当时大一统的趋势所刺激,而主张定于‘一’;故只讲王天下,不讲霸诸侯;只教人帝制自为,不教人当什么诸侯之长,这和孔子的思想已显有差异。另一方面他把王霸二字赋予一种新意义,不从地位上区别,而从性质上区别,王道霸道,判然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中心地位的王霸论遂出现了。”[《嵇文甫文集》上,第18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表明儒家对“王道”、“霸道”的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战国末期,“王霸”、“德力”等相对性观念,就不象在孟子那里,表现出比较尖锐的对立和冲突。面对当时的形势,荀子也不象孟子那样,对“霸道”不屑一顾。荀子晚年游秦,当秦昭王时。秦国经历了孝、文、武、昭四代,正是战国霸道的先驱。荀子观察当时的秦国,曾经给了秦国一些正面的评价。范雎问荀子“入秦何见”时,荀子首先指出秦国的“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等有利的自然条件。然后对秦国的政治情况表达了赞美,说秦国的百姓纯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对官吏敬畏和顺从,是“古之民也”;大小官吏都庄重严肃,恭俭忠信,是“古之吏也”;士大夫不结党营私,都通达奉公,是“古之士大夫也”;朝廷在退朝时,各种政事从无遗留,恬然如如无治者,是“古之朝也”。所以,自秦孝公以来经历了四代国君,不断取得胜利,“非幸也,数也”。他甚至说:“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确实给予秦国以很高的评价。但到最后,他又话锋一转,明确指出:“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如果说荀子当着范雎的面对秦国的批评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他在别的地方对秦国的批评就毫不客气了。这些批评归结到一点就是秦国不实行礼义,而专靠暴力。他说:“力术止,义术行。曷谓也?秦之谓也。”(《荀子·强国》)认为秦单靠武力的方法其胜利是有止境的,而通过实行礼义提高威望则是更为重要的。所以,秦单有“霸”和“力”,还不够理想。理想是什么?最终仍是“王道”。换句话说,荀子谈论“霸道”,是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的,他理想中的社会制度依然是以礼教为本,以强力为辅助的。
有鉴于秦国的霸政的不顾理想,荀子对王霸进行分疏:“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霸。”(《荀子·议兵》)通过比较两种不同的强国之道,荀子对以德兼人与以力兼人,即对王道与霸道的内涵加以分疏。他说:“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荀子·议兵》)“以德兼人”,国家有向心力,君主有号召力,百姓甘赴国难,得到土地能够控制得住,得到人口可以强兵,这样就能真正地增强实力;反之,“以力兼人”,不是由于名声和德行的吸引力,而是慑于统治者的武力,暂时依附,其心并不服,国家没有凝聚力,得到土地也不一定控制得住,得到人口却需要更多的监控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尽管可以建立暂时的威权,其势力却注定不能长久。
荀子对王霸还进行了更细致的辨析和发展。他在王道、霸道之外,又分出了一个“强道”:“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荀子·王制》)在《荀子·王霸》篇中,他又将这三类政治所代表的政治道德分别概括为“义”、“信”和“权谋”:“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将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就不难解读了。“夺之人”,是争取人心,靠的是仁义,为王道政治;“夺之与”,是结好诸侯,靠的是信誉,为霸道政治;“夺之地”,是攻城略地,吞并邻国,靠的是权谋和气力,为强道政治。王道、霸道、强道都会带来各自的政治后果。行王道者王天下,这便是“臣诸侯者王”,“义立而王”。行霸道者称霸诸侯,这便是“友诸侯者霸”,“信立而霸”。接下来的“敌诸侯者危”,“权谋立而亡”,都是行强道政治的后果。荀子认为这是一种亡国之道,万不可取。这里可以看出,荀子是立足于现实,根据当时实际状况分疏王、霸、强(亡),这主要是社会发生了变化的缘故。这样,荀子以否定之否定的辨证逻辑的“三分法”超越了孟子以“王霸”二元为主的“二分法”,使历史与逻辑在这里统一了起来。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他兼王霸的王制。《荀子·王制》:“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诸侯莫不怀交接怨而不忘其敌,伺强大之间,承强大之敝,此强大之殆时也。”所以荀子说:“秦四世有胜,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所以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矣。”(《荀子·议兵》)为此,荀子主张兼用王霸而取二者之长,主张“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荀子·议兵》) 荀子描述兼王霸之治说:“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荀子·富国》)用王道,则“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用霸道,则“辞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荀子·王制》) 可见,所谓“兼王霸”即认为单纯的王和单纯的霸各有长处,又各有不足。单纯的王可以存国安民,而不可应变创业。单纯的霸足以兼并而不足以坚凝。兼王霸就是主张兼取王、霸的长处,而弥补其各自的不足,要在保持王道的基础上采用霸道,以创业应变。[张京华:《儒家思想的转变:荀子和韩非》,孔子2000网站。]荀子是主张以王道为理想,王霸并用,德力兼行。
他还说:“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荀子·王霸》)这里把王道、霸道作为治国安民的上下之策,说明荀子尽管给霸道以适当的肯定,但他并没有把霸道与王道并列起来,王道为上,霸道为下,二者的主次关系是清楚的。他还说:“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荀子·王制》)“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荀子·议兵》) 从这些议论来看,王道毕竟还是荀子的最高理想,他从没有把二者等同起来。因此,有论者说:“荀子认为王霸只是治法上的不同,是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区别。”[钟肇鹏:《孔子研究》(增订版)第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还有人说荀子是肯定霸道,甚至称许霸道,把它当作王道的次生形态、过渡形态、补充形态的。[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第363—36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费孝通论王道与霸道云:“儒家希望政权和社会本身所具的控制力相合。前者单独,被称为霸道;相会后方是王道。”[费孝通:《皇权与绅权》第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些论说颇得荀子思想的精义。荀子的王霸并用最能显示他思想的本质特征,童书业认为:“荀子的思想通过韩非、李斯,颇有影响于秦朝的政治,而汉朝的制度有许多是继承秦朝的。汉朝所谓‘王、霸杂用’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阳儒阴法,而荀子便是一个儒家大师中‘阳儒阴法’的人;必须明白这点,才能抓住荀子思想的本质。”[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第173页,齐鲁书社,1982年。]
孟子认为王霸的不同是种类的不同,是互相对立的;荀子认为王霸是一类东西,仅只是走得彻底不彻底而已。王和霸的不同是彻底上的不同,不是种类的不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第679-68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孟子侧重从超越性的政治理念层面看问题,所以把王霸对立,尊王贱霸;荀子侧重从现实政策操作方案层面讨论问题,所以不把王霸对立,他尊王不贱霸,认为霸不如王但亦有一定价值。孟荀对待王霸的态度和观点上的差异,成为孟子竭力反对法家,荀子适当兼容法家的不同学术思想取向的根由,也开启了后世儒家内部王霸争辩的序幕。
总之,从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上讲,王霸之辩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五)有治人,无治法——人法兼取
先秦儒家主张的“人治”,其思想渊源于西周礼乐文化,其基本的观点是“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孔子所倡导的贤人政治是其德治、礼治主张的逻辑延伸。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在强调“人”还是强调“法”这一点上与儒法形成对立。荀子继承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传统,对法家“垂法而治”的主张不以为然,他批评慎到“弊于法而不知贤”( 《荀子·解弊》)他还在《荀子·非十二子》批评作为法家的慎到和田骈说:“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针对法家一断于法,不能尚贤的缺陷,荀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系统的理论阐述,他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提出“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王者之人”即能用礼义约束自身,循法理政,明察善变之人;“王者之制”即传统的宗法等级制;“王者之论”指基本的政治法则,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则是指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荀子·王制》)。这四个方面,既是君主努力的目标,又是衡量君主的标准。这依然不离“贤人政治”的范畴,而荀子不过是煞贫苦心地为君主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境界。荀子将这些总结为“有治人,无治法”:
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君道》)
就这一段话来说,荀子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第一,任何法都要靠君子来实施。法度作为社会规范,自己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要靠人来推行和运用,离开人,法就会失去作用。他举例说,后羿射箭的技术尽管还存在,都不是世代都有像后羿那样的人。第二,君子为法之原,有是人而有是法。法是治国之端,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比较起人来,君子则是法之源泉,更为根本。有了君子,无法可以有法。因此,法是治道之流,而非治道之源,君子才是真正的治道之源。就人与法的关系而言,他认为只有决定一国之治乱的人,没有离开了人而能治好国家的法度。法是靠人来制定的,人的善恶决定了法的优劣;法又靠人来执行的,人的才德直接决定了法在实践中的得失。显然,这样的认识无疑是很深刻的。这里的“人”,首先就是圣王和君主。“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如果“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荀子甚至断言:“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这种对“人治”政治本质特征的概括并非全无道理。荀子是礼法统一、儒法合流的先行者,然而在这一点上仍不失儒家立场。[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第236-24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对此,肖公权指出:荀子“凡此所言,皆与孔子之意合,而足见荀学之根本异于法家。盖法家寓君权于械数之内,荀子则欲君主之人格透露于法制之外。前者专重法治,后者则求治人以行治法。此人法兼取之说,实亦直承孔子遗教,而非荀子所创新。”[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10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这种“人法兼取之说”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难以落实,说明荀子理论本身也有问题。正如肖公权所说的:“然而一考其实,则当世之君或为其所及见者,齐则威、宣、湣,燕则子喻,楚则倾襄,赵则孝成,秦则昭襄,凡此诸君之中,无一可为荀子治人理想之根据者。及至秦汉以后,曲学之儒,窃取荀子尊君之义,附以治人之说,阿君之好,极尽推崇。流风所播,遂至庸昏淫暴之主,不仅操九有之大权,亦得被重华之美号。以实论名,贻害匪浅。此虽荀子所不能逆睹,而其立说之有未安,亦由兹可以推见。”[肖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一)第109-11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确实,必须看到,荀子提倡的人治也存在严重的弊端。首先,将人置于法之上,把法看作是圣人和君子治国的工具,否定法外在于人的客观标准,也就否定了法具有的独立的价值和功能。其次,不在法的基础上发挥人的能动性,必然会造成立法、司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就会损害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消弱法的权威地位。第三,理论上,人治是通过圣人和君子实现的,而在实际上,作为法的化身的不是圣人,而是专制君主,朕即法律,具体操纵法律的也往往是一些权臣法吏,甚至酷吏。[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第18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四、三、荀子治道的现代价值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赞扬孔子、子弓:“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敛然圣王只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这未尝不是荀子的自道,说明他生当战国末期,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以统合各家自命。他的学生甚至认为荀子贤能超过孔子:“孙卿迫于乱世,鳅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剌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弊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声名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仪表。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荀子·尧问》)荀子尽管一直以儒家正统自居,但历史上,不只一人将其视为儒学异端。唐代韩愈称道荀子为“大醇而小疵”[韩愈:《读荀》。],宋代理学崇孟抑荀,指责荀子为“异端”,如二程说他“悖圣人者也”[《二程遗书》第25卷。],朱熹谓:“荀卿则全是申韩。”[《朱子语类》卷137。]对荀子的学术思想地位虽然不能象其弟子一样过分赞扬,但是也不能象唐宋以后那样过分贬低。我觉得,《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为公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
荀子对治道的重构是经过了春秋战国学术分化,百家争鸣,学派交融之后,便特别具有整合百家的优势。从理论的演变进程来看,荀子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德力”、“王霸”以及“人法”之争作了批判总结,形成了集大成的治道思想体系。这些思想遗产,为汉代新儒家发挥,为汉代统治者应用,成为汉代,乃至其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采用的治道模式。因此,到了近代,才有谭嗣同“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谭嗣同:《仁学》。]的说法,这虽然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实际上正是对荀子治道思想的实用价值和历史地位的准确概括,也揭示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奥秘。
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加速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的全面崛起令人振奋。但是,无庸讳言,当代中国的治道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道或者价值的缺位。当代中国的治道是有法有术而无善治之道,没有传统的道统与政统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第二,即使治法治术也未能形成系统,不同层面未能互相融通、协调和配合,这大概与条块分割的体制有关。
第四,政府机能僵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各层面竞争失衡,发展失序,缺乏自治功能,一方面消极被动应对政府,另一方面积极主动谋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造成失衡不公,无序、内耗、浪费、破坏严重。
第五,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事事都要自上而下,层层下达。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型,它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国内治理危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法制建设危机重重、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党群关系日益紧张等等。治理危机的出现给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侵蚀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有可能把中国带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中断。”[崔顺伟:《治理危机与当代中国治道变革》,http://www.setgid.com]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新世纪的发展挑战:2020年的中国》说,在2020年,中国可能有两个前景,一是“中国僵化症”发作,中国依然是低收入的国家,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将会增加,城市也会出现贫困,落后省份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消除贫困,穷人和名流共同生活在城市里,名流左右法律和制度为自己服务,城市成了火药桶,外国投资减少,贸易摩擦和报复增加,国际贸易陷入困境。二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时中国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充满关怀的、自信的、已经消除了今天意义上的贫困的、能为孩子们创造美好健康未来的国家。中国的未来就在我们是手上。这就需要我们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如《易·系辞下》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进行治道变革。怎么进行治道变革?沈家本在主持清末修律中就指出:“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源,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道,庶几采撷精神,稍有补于世。”[沈家本:《寄文存·政治类典序》。]这里仅就几个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应该重视传统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视对传统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此,本人曾经提出以儒为主,整合多元思想文化的思路[《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学与中国文化的整合》,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庞朴主编:《儒林》第二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在儒家当中,荀子是宋明以后因偏见而相对贬低的儒家学者、思想家,近代以来相比较其他儒家人们对他研究也很不够,他的思想最有价值的正是治道方面,这方面正可以使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与西方现代法治为主体的治道进行沟通、接隼,其许多思想还仍然是有价值的。
其次,确立文化主体意识。“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一切都应透过具体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如实地评估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制度,进而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纳,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朱高正讲康德》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即就是在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治道思想和经验,构建中国现代治道体系。
第三,复兴传统礼乐文化体系和礼治治国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配合。礼在古代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一个道德与法律、道德与信仰、道德与哲学、道德与政治等交错重叠的网络状结构体,礼治在中国传统治道当中起着巨大的而全面的社会整合作用。众所周知,我们前几年一度掀起了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讨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更没有得到落实,这里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说,没有提及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西方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以宗教与法律为主体,辅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谓道和形而下之谓器的二元对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中道制衡作用。前几年的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提法,是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试图把中国的德治与西方的法治结合起来,但是由于没有礼治作为主体,居中制衡,向上沟通道德,使道德能够落实,向下沟通法律,使法律有所统摄,所以,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就只是纸上的谈兵,纯粹逻辑的思辨,没有办法成功。
可喜的是,新一代领导人掀起了一场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治道变革”。而这场变革的核心就是重提儒家“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强调在新的时代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种价值观,此次变革的突出任务就集中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例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将为此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作者:韩 星,陕西蓝田人,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教授,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及儒学、儒教研究。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邮编:100872
联系电话:13511087238
电子信箱:lthanxing@163.com
上一条:性恶论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