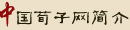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姚海涛】荀子对智性的阐扬及其与科学的关系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原载于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摘要:从近代荀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出发,会发现荀子研究总是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随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牟宗三先生以重仁与重智的二分疏解儒家哲学两大系统,广义敞显了荀子继承自孔子以来的智性主义,认为荀子发展出难能可贵的与西方重智系统相近之学术面向。《荀子》写作方式、天人观皆透显出其对智性的大力阐扬。建基于此,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呼之欲出。前贤对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概有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三种观点。其中关联说最为客观中肯。无论是从荀子逆向重智所凸显的不占、非相、解蔽,还是从荀子顺向重智所标举的礼智对显、辨合符验与物理可知,皆可见其推阐智性之良苦用心。平情地讲,荀子重智构成了从宗教而人文而科学的逻辑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仍当归类为人文理性而非科学理性。因荀子已将人文理性发展到顶峰,若非受到后来历史之大冤屈而湮没,由此而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顺适走向科学理性并非天方夜谭。
关键词:荀子;智性;科学
引言
当今学界,荀学研究已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重镇。而荀学之沉浮起落,可从中国哲学史上窥见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由此可梳理出一条隐潜的荀学史脉络。荀学远绍自孔子,肇始于荀子,在其后的思想历史中虽未曾位居主流,甚至难称支流,更有甚者,被视为歧出与异端,但始终未断流。这便是荀学的思想韧性。而此韧性,自荀子批判诸子,熔铸百家,以道自任之时,便已种下。
如果将孔子视为内圣外王的合一与仁智合一的学思行谊之典范,那么,孟子与荀子则各侧重继承其一面。孟子思想独标内圣,高蹈仁义,成就了中国哲学早期的亚圣形象。而荀子思想则重视外王,凸显智性,成就了中国哲学早期的学宗形象。此本是中国哲学早期发展中的二水分流之正常学术现象,孰料却因后儒道统之争而使孟荀呈势不两立之态。有宋以来,孟子之道大昌,荀子之学不彰。
然而,现实是一股力量,一股无法逃离的巨大力量。包括荀子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从来不会脱离现实,总是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投射在抽象的理论探究之中。历史是公正的,思想家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时代淘洗中沉淀,在思想流变中再生。在漫长的哲学史中被视为异类,却在近代思想观念剧变中重被发现、认可、阐扬,荀子即是显例。而这缘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背景与当时学者的问题意识。
一、近代荀学研究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外来文化冲击不断。其中最为强劲的是,西方民主、科学的时代巨浪已然席卷世界,对彼时的中国带来了天翻地覆式的冲击。有识之士认识到,此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故找到破除阻碍民主与科学传播的文化因子而去除之,或者寻觅到传统文化中的近似资源以辅翼之,皆将对旧中国开辟现代路径助益良多。中国本有文化的去留存废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传统学术能否与西方学术接轨,能否产生新的研究路向,能否赋予更多的可能性等等,遂成为当时学者的问题域。回归先秦,找寻相关思想资源,无疑是一条历史上久已验证过的有效途径。有识之学人,为接引西学,延续中学,辗转求索。所谓物极必反,真妄毕见。简言之,近现代学术渐起,成为这一阶段的显明学术特征。
诠释空间的获得有赖于诠释视域的打开,而视域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主题之转换。遥想当年,在时代主题转换的战国时代,围绕“救弊治世”(牟宗三先生语)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盛况,而荀子集其大成。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近代思想史上出现了尊荀与排荀之共存并争,一时竟势同水火,促成了观研荀子的新论域,开出了精彩纷呈的新荀学。在现代学术视野之中,出现了“荀子回归”运动。跨越千年的思想历史,荀子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贯穿于其中。近代以来,研荀者既多,性恶性善,科学民主,厘清研判,新意迭出。
近代荀学从荀学史脉络中走来,自带深沉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史概念登上学术舞台,足以成为荀学史、荀学研究史上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近代学人之学思延续着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意识,面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有着透辟而深邃的思考。排荀尊荀,各取所需,不为无见。按照江心力的分类,近代荀学可分为二十世纪初的荀学、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荀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荀学研究三类[1]。此分类比较驳杂,贯穿了时间、历史事件与研究方法。若以研究范式来对近代荀学研究进行分类,则可分为两类:训诂荀学与义理荀学。因训诂荀学与近代史的社会背景关联度并不直接,故仅以义理荀学之开展为例,展现荀学研究之问题意识可也。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认为荀子代表了专制,成为绌荀尊孟之急先锋。谭嗣同则视荀子为“乡愿”,进行理论挞伐。章太炎则尊荀子为后圣,高度评价,推崇备至。作为变法政治家的梁启超与谭嗣同从当时国家走向民主的途路角度,将荀子视为一绊脚石,其认知理路是扫清中国思想史上专制之因子,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但视荀子为专制之代表者的观点却值得商榷。此类观点,无疑将荀子在思想史上“大本已失”之冤屈基础上更增一层“专制”罗幕,仅因变法之需而将荀子立为“靶子”,绝非理性客观之研究,故其观点实不可取。
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近代学人多从中西比较对勘的视野去研读荀子。西方思想文化最为近人所激赏者,当为科学与民主。如胡适、王恩洋、牟宗三等学人皆有功于荀学。近代荀学研究的其他学人如杨筠如、陈登元、陶师承、熊公哲、杨大膺、冯振等皆有研荀专著,限于篇幅及其学术影响力,故不在此加以论列。
胡适将先秦儒家分为两截:荀子以前的儒家与荀子的儒家。这足以说明,胡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荀子之于儒家的非凡意义,确实是一个新发展,与思孟一派儒家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胡适提到了荀子的心理学与名学等,这在荀子之前的儒家属不太重视或成果不多的论域。胡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研究荀子,开出了一片新天地。而在对“哲学史的史料”“审定史料之法”“整理史料之法”中多称引《荀子》以证校勘,足见其意识到了荀子思想话语中的求真意蕴。其研究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说运用得淋漓尽致,真是一场思想考古之旅。
近代荀学中一位被忽视的学者是王恩洋,一部被遗忘的著作是《荀子学案》。王恩洋处于西南一隅而不显,加之其蜚声佛教界,以佛教研究著称,故其荀子研究,向为学界所忽略,而未能抉发其深厚意蕴,未显其应有价值。王先生有对佛学的深湛覃思与笃定信仰,有长期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经历,对于包括荀子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有较为清醒、系统而全面的认知。从其书“学案”的命名来看,似乎尚未摆脱黄宗羲学案式写作、疏义式写作的窠臼,实则为思想史传承意识使然。观其视野、方法等早已经迈进了现代学术研究之列。如《荀子学案》十三篇之中有“评论”一节者,计有正名第八、论性第九、论天第十、论政第十一。何以故?实为写作先后之不同,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写作范式,又其所论者为荀子重大理论问题故也。王恩洋视荀子为经验论者之代表,以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视域[2]去审视荀子。从世界文明思想史的宽广视野中对勘荀子,从中华文化思想史的纵深视野中去衡定荀子,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立论至精,定位甚洽。其研究视域开阔,在打通中西、古今、佛儒的基础上,融汇贯通为一炉,是近代学术史上为数不多的识得荀子好处的研究者。
从后来研荀的学术影响来看,当以牟宗三先生为最大。牟先生的荀学研究若置于荀学史的背景之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时贤所处之近代中国,所缺乏者正是民主与科学。荀子又似无民主而有科学,孔孟似有民主而无科学。牟宗三撰《荀学大略》专书以明之,并在《历史哲学》等诸多著作中一再论到荀子,认为荀子之客观精神正可对儒家传统补弊纠偏,认为荀子是逻辑学之早期代表,是中国智性传统之杰出代表。牟宗三研荀的具体观点则在后文详细论及。
近代荀学研究从开出民主与科学的角度言荀的基本思路与其所处的时代课题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荀子之所以重新“回归”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后来荀学之湮没,是中华民族之不幸也。然其建构之精神实令人起庄美之感,足以医后来贫弱之辈,视国家政治为俗物,视礼义法度为糟粕,而自退于山林以鸣风雅,自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知已奄奄待毙也。”[3]218-219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脉络角度去衡量、论定荀子这位曾被打入另册的思想家,尤其从“科学”这一近代乃至现代影响人类生存样态的核心概念出发去研究荀学,话题重大,意义深远。近代荀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荀学研究范域,不但大大地推进了荀学的现代性,而且促成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荀学研究在对古老话语的现代转换方面进行了若干有益探索,在打通古今中外的思想关联,探索人类普遍性的思想方面做出了颇有力的贡献。由是,近代荀学成为荀学史中较为特殊的阶段。
二、重仁、重智的二分与荀子重智的敞显
(一)儒家的两大系统:重仁与重智
牟宗三先生作为较早进行荀子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从中国哲学史的宏大视角来分析孔子、孟子、荀子。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并存着重视主观性原则与重视客观性原则的两条思路。”[4]具体到天人关系,“孔子所说的天比较含有宗教上‘人格神’(Personal God)的意味。”[5]牟先生以超越的遥契来解孔子,以内在的遥契来解孟子。固守主体性原则是孔孟所共许之关节。显然,荀子与孔孟入思路向迥然不同。牟先生认为,荀子开出了中国哲学史上与重仁不同的重智传统,故需以客观性原则解之。孔子从超越的遥契而生出敬畏意识,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孟子内向超越的理路,其涵蕴的对天道的企思追慕与神秘冥契式的存在体验,无疑具有神秘主义气质。而走出神秘的关键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方式。孔孟对主客关系的处理是“客体是通过主体而收摄进来的,主体透射到客体而且摄客归主。”[6]而这是儒学思想史上判定儒家正宗与歧出之关键所在。荀子对智的高度推许与孟子对仁的抉发二者截然不同。值得指出的是,荀子讲“仁知之极”,讲“仁知且不蔽”,均将仁与智同重并列,并非仅重智,也重仁。至于仁之是否仅能植根于性,则是另一学术问题①。公允地讲,与孟子相比,荀子更大的思想贡献在重智。
综观牟宗三的思路,其扬孟抑荀、综合判教的价值立场没有变,以尊仁为宗,认仁之境界高于智之境界的观点没有变,所秉持天人性命贯通之圭臬没有变。牟氏显发荀子哲思意蕴仍是隐于孟子羽翼之下的彰显,犹以荀子大本未明,需辅以孟子向高处提。此以荀就孟的立场,仍未脱宋儒之讥荀子的意思与立场。在牟宗三看来,重仁为儒家正宗,高妙圆融,而智之一系,虽高明但未致中庸妙境。牟先生以华族慧命相续之用心苦则苦矣,可惜的是,客观同情之了解变为了预设立场之判教,以境界高下判中西与孟荀,鼓荡文化偏执之自信,未为可取也。所谓,其意虽美,行则未善也。
(二)《荀子》写作方式与重智
从《荀子》的成书方式来看,其与《论语》《孟子》的成书方式有着绝大不同。《荀子》的成书不是在本人殁后或晚年经由学生及后学整理而成,乃主要由荀子本人亲自写作而成,体现出了荀子早期、中期、晚期的阶段性特点,甚至暮年之时的荀子仍在不间断地创作,可能对作品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编订。
从外在形式来看,《荀子》中的多数篇目已经有了学术论文的面目与性质,甚至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文题目。此亦不似《论语》《孟子》二书般从篇首之句择取二三字为题。《荀子》可谓先秦诸子论著中之特出者。从语言辞彩来看,其中佳言格论层出,理论思辨严谨,具有文学与哲学的张力,文章铺排有序、有理、有势,众多修辞手法并用,堪称巨著名作。从涉及内容上看,其论域宽广、涉猎广泛,论题选择独运匠心,直指时代弊病。百家学术争鸣中的诸多重要论域、论题,《荀子》中皆有论文以回应。如天人观之《天论》,认识论之《解蔽》,逻辑学之《正名》,人性论之《性恶》,政治学之《强国》《富国》《王制》《礼论》等。
由此可见,荀子思想旁赡博赅、博大精深,其所回应时代论题之广泛与精到,体现出了系统化、精细化、理论化的鲜明特点。这些特点显然均与荀子重智的理论徼向与学术思理密不可分。
(三)荀子天人观与重智
天人关系作为中国哲学元关系在诸子争鸣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天”不仅有自然义,而且有着比自然更为微妙难言的复杂意蕴。由于天人关系涵摄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遂使其成为检验哲学上是否为可知论及可知限度的一块试金石。荀子天人观充分显示着其经验主义,体现着重智的理论倾向。
1.天生人成的基本原则
牟宗三先生对荀子研究的一大贡献是将“天生人成”一语拈出作为“荀子之基本原则”[7],认为荀子学术大端为客观精神与认知上的逻辑心灵,与西方重智系统相接近。牟氏指出,“荀子之思路实与西方重智系统相接近,而非中国正宗之重仁系统也。”[8]“相接近”一语是为得之。荀子与西方重智系统是否一致,是另外一个问题。而由天人观来透视荀子是否重智却是极具可行性的研究思路。
牟先生对天人观的解析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相对合理而稳定的观察框架。韦政通先生沿习牟氏理路入乎其内,分而析之,析而裁之,详尽地构造了荀子“天生人成”原则[9]。成中英先生则将荀子视为“统摄天人之道的系统哲学家”,从人性、语言、知识、道德和政治治理五位一体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荀子将自然与社会统而一之的思想大脉络。成先生认为,“系统、正确地理解荀子思想之核心概念的关键在于充分认识荀子于天人之间所作的区分与联系。”[10]无论是牟先生所认为的荀子沿重智路向而产生的天生人成之大原则,还是韦政通先生将荀子天生人成的理想定义为人文化成,抑或是成中英先生所认为的荀子“统摄天人之道”,无疑敞显出天人观之于荀子哲学体系的重要性。沿着天人关系路向,走入荀子之思无疑是一条通途。天人观足可成为宏观把握荀子的重要抓手,成就荀子之所以是荀子的重要理据②。由此出发,把捉荀子真意,打开荀子全幅思想方成为可能。经过牟宗三为首的前代研究者的阐扬,“天生人成”与“礼义之统”③几成为荀子研究中的不刊之论。
2.阴阳之气与自然之天
作为宇宙论范畴的阴阳概念是战国时代自精英到大众的普遍话语。陈来认为,“春秋时代‘气’和‘阴阳’之气的观念在智者群中已普遍流行。”[11]阴阳早在春秋之初的伯阳父论地震时作为诠释地震之所以产生的两股力量表征已被熟稔运用。先秦诸子所用概念之间的差异并未如汉代以后的思想史中所言说的那般巨大。荀子并未对阴阳、气等观念进行详细定义与辨析而直接运用之,说明当时此类观念已普遍为知识精英所接受,而不必详加解释。观察《荀子》之前的《庄子》等典籍可见,这些观念构成了当时知识精英对话、立说不言自明的基本知识背景,属同一文化母体孕育而出的共同话语体系。
荀子所论“阴阳”仅有“相阴阳”一语之“阴阳”为阴阳五行、宗教迷信之事,并批判之。其他的“阴阳”皆无此义,全为自然义之“阴阳”。而对于鬼神、巫术的批判无疑表现着荀子重智的一面。荀子以阴阳来解天地与万物,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12]天地、阴阳、性伪作为相对反的概念,连接了自然与人为两大界域,成为天人观的重要观测点。
在荀子看来,自然万物莫不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此正是《周易·说卦》所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13]后来宋儒陆九渊亦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14]天不过是阴阳二气交感作用的结果。天地流行而生万物,万物因气共质而相通。天即存有即活动,能命万物,能赋人形,能成人性,故人需要践行天职。荀子又云,“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15]从中不难看出,荀子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推崇,对取象观念的运用,其为易学传人必矣。学界流行的以所谓“天人相分”解荀子的观点,实大有问题。儒家天人观确实与道家迥然不同,总体上有向人而非天的倾向。学界通常认为,在天人观上有天人之分与天人之合两条思路。然而,分与合不是截然对立的,分离与分享并非截然分开。应当承认,荀子天人观中的分离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但决不意味着其不存在天人相合的意蕴。他认为,上中下、天地人,三才横亘于宇宙之中,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整体。所以,建立在西方哲学框架下的所谓主客观分析来衡断荀子,无疑是方枘圆凿、扞格难通。
3.宇宙景观与社会秩序
直面悠悠岁月,对望青苍天穹,荀子没有产生渺小意识反而生出知天、制天观念。这无疑需要理论勇气,这深深根植于思想家厚重的理论造诣之中,也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赋予人的力量。若不承认荀子对人文理性的追求,就无法理解“君子以为文”的卜筮、“志意思慕之情”的祭祀与“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等独著异彩的观点。卜筮、祭祀是文,是情,是人文。理是道之理,是天之理,是自然。荀子将天人间的神秘关系藉由阴阳、气等物质性观念而得到稀释、解构,进而达到重构与塑造。荀子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景观因解释模式、架构范式的改变而与前人的天人观大异其趣,由“可畏”而“可爱”进而变得“可信”。“可信”正是智性的表达。
荀子将社会秩序与宇宙景观并驾齐驱,直接将天人同列而无需通过内在超越的神秘方式来实现天人合一。他将天人相分贯彻到底,理清天人各有其职分,如此便可充盈鼓动主体,将主体价值放大、凸显,将原本匍匐于天的脚下之人的主体性挺立起来,使人跻身于天、地之列,成为天地人三才之对局,以与天地万物构成生命共同体。从天人相分而不是浑沦的天人合一角度去显发人之为人的主体性,让主体具有了争夺人之为人的“天然权利”,这确是荀子不同于孟子而重新架设的不同理论路径,是思想理路与文化脉络的创新与进步。虽然直截,但并不突兀粗暴,而是整合了无神论、自然论之路开辟出的文化新路向。
天作为价值支点与意义源头的不断弱化,神秘意义的减损与消褪,从神格、人格义再到道德义理之转化,在社会政治中由实位化为虚位,再到自然之天,这是思想史逻辑发展之必然。人作为“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必然参赞天地之化育。“礼义之统”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格局的开出是由天到人的逻辑。在现实的政治化生存世界中,天时、地利、人和在圣人制礼作乐中得到有机合一,形成中华民族“礼义之邦”一以贯之的文化心理结构。荀子作为儒家人文主义早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对宗教世界的解蔽祛魅与安顿重塑表现在对天上人间关系的重新梳理,实现了天人关系上的重大思想突破,是理性主义的重大敞显[16],同时,荀子对人与社会之间世俗关系的礼乐化塑造,实现了人间差等秩序的礼义化。
三、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
在近代学术话语中,荀子因重智被重新发现而“回归”,因与科学间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而受到推重。但荀子是否为科学主义者,或者说荀子思想离科学到底有多远,则是一个有学术争议的问题。不少研荀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大致讲来,基本有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荀子与科学关系的三种观点: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
其一,肯定说。此说肯定荀子思想与科学间的紧密联系,甚至认为由荀子可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荀子《天论》中的这段话,向来为学者所重视。兹引如下,“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7]学者陈大齐解释此段时云,“荀子这一番话,可说是其自然学说中最精彩的言论,亦最值得后世所重视。荀子欲物畜天地而役使之,欲骋人的智力以增益生产,此与西洋人所向往的征服自然,初无二致,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神,亦甚切合。假使荀子此一学说而见重于后世,有人为之发扬光大,则今日中国的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纵不能居于世界领导地位,亦决不至于落伍如此之甚。所以荀子学说的湮没无闻,实为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18]王恩洋氏亦有类似看法,他赞叹道,“(引者注:荀子)征服自然以利人事之思想,彰明较著如此。近数百年科学兴,人智进,始有如是主张。而我先哲于二千数百年前言之,伟矣!”[19]。再如鲍国顺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荀子的自然论,无疑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同时也是荀学中最为突出的部分之一。《天论》一篇,文理绵密,议论周延,即以科学知识如是进步的今日衡之,我们仍不得不深致佩服之意。”[20]肯定说大多从征服自然的角度言荀子思想之科学性。是否只能从征服自然角度言科学是一问题,而荀子又是否以征服自然为目的,则是另一问题也。荀子果持人定胜天的观点吗?恐未是。其明确天人之职分是为了让天归其天、人归其人,属天人之辨的一新阶段,并未有天人交战而人胜之之意。
其二,否定说。此说否认荀子思想与科学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较大差距。如胡适曾以戡天主义视之,认为,“荀卿的‘戡天主义’,却和近世科学家的‘戡天主义’大不相同。荀卿只要裁制已成之物,以为人用,却不耐烦作科学家‘思物而物之’的工夫。”[21]胡先生大约以名家为科学家,而将荀子对名家的攻击视为反对科学的态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胡适在他处解读荀子“大天而思之”一段时观点有所游移,或说改变——“第一要教人征服天行以增进人类的幸福。第二要人勿须问万物从何处来的,但研究万物的性情变化,便够了。第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是科学目的,第二(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是科学的方法。”[22]韦政通则认为,荀子的人格接近希腊哲学家的智者类型,但其思想未向知识论发展,也没有完成一套知识论哲学,当有助于早期科学的发展[23]。荀子的科学心态属理智主义,在理论上有一定意义,而在实际的科学进展中反不如神秘主义(引李约瑟语)。荀子的理智主义与其不可知论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阻止了其向科学方面进一步发展[24]。这些学者虽然看到了荀子的经验主义特质,甚至揭示出其批判精神,但认为荀子的智性精神并非近代科学精神,甚至也不能开出科学。
其三,关联说。此说认为荀子与科学存在些许关联,但不认可由荀子思想可直接导引出科学。牟宗三对《正名》篇进行疏解后认为,“荀子实具有逻辑之心灵。然彼毕竟非正面面对逻辑而以逻辑为主题也。此乃从其正面学术拖带而出者。”[25]此说确有其道理。由于逻辑与数学为科学之根基。逻辑是科学产生的理路与前提,若无正面之逻辑则不会有真正之科学。易言之,荀子的逻辑心灵非正面面对逻辑,并非为逻辑而逻辑,为科学而科学者。虽与西方重智传统相接近而与其并不相同,未若其纯粹也。其智之面向主要并非针对自然而是人群社会,故荀子成就之大端在礼。礼义之统的重视使得其知统通类的纯粹逻辑学意义大为减损。
牟先生对荀子之天作了辨析,认为“荀子之天非宗教的,非形而上的,亦非艺术的,乃自然的,亦即科学中‘是其所是’之天也。”[26]在解释“天职”时,又云,“不加虑不加能不加察之‘不与天争职’是一义,于治之之中而知之又是一义。后者有类乎杜威义之科学,前者则去无谓之希求怨慕,惊惶恐怖。”[27]牟氏从基本精神与心思形态角度对荀子进行剖析梳理是其高明之处。故其看到荀子的逻辑之心灵、名数之灵魂,断定荀子为接近西方重智系统。基于此,牟氏捎带对宋明儒学之山林之气有所贬抑。此等方面,皆正中荀子思想。疏导、融摄荀子以辅翼民主科学之开出,确实是牟宗三思想接引西方科学一条路径。吊诡的是,牟宗三对荀子在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判教式定位,对科学某种意义上的轻视,反倒使得其对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认知颇为恰切。荀子的思路必然需要重新调整顺适而转进,方能臻于科学理性之路。
(二)荀子何以“科学”之逆向重智:不占、非相与解蔽
从天人观不难看出,荀子重智性、重经验、重自然的思想倾向。而其不占、非相与解蔽的人文视域与重智密切相联,且是彼时神秘主义氛围的逆向反应。荀子所处年代正是战国中晚期的神仙方术思想大兴之时。当时燕、齐两国方士甚多,诸侯王信奉者众,于普通民众中流传甚广。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还专撰《龟策列传》,对卜筮的作用进行了肯定——“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28]。与此同时,稷下黄老道家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独特体认与形神关系的理论建构,发展出了顺任自然的重生、养生之术,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形成做好了思想准备,与燕、齐方术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应。“巫祝”“禨祥”一类方术的流行,足见当时迷信方术的社会风气之盛。
巫史不分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直到周代,仍能见其影响。如周代文献及铜器铭文中所展现的思想演进中保留了祝、卜等知识系统与思想观念。早期儒家与巫文化之间确有渊源关系。陈来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经历了夏以前的巫觋文化到商代祭祀文化再到周代礼乐文化的嬗变过程[29]。儒家甫一成立,就在孔子的带领下,以人文理性对巫文化排斥和挤压,展开了“脱巫”的行动。故帛书《周易》《要》篇提到孔子之言云,“吾与史同涂而殊归也”。孔子已经看到儒与古代巫史系统的内在关联,已然意识到二者殊归。此殊归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野。小人儒是柔弱的,是以祈禳、卜筮、祭祀之礼为职业的谋生之儒,而君子儒则刚健有为,有更高理想追求,是事业担当之儒。
无论是“善为《易》者不占”,“非相”,还是“解蔽”等,均体现出荀子重智性、反巫觋、辟鬼神、明真理等逆向重智的思想面向。荀子对巫占的批判既是儒家“脱巫”传统的延续,又是礼义系统的重要建树。荀子在延续古老思想传统礼的同时,又与巫划出一条壁垒分明的界限。在荀子视野之中,“禹行而舜趋”的子张氏之儒,模仿禹步,可能正从事着巫所从事的行当,有回复到巫术时代之危险,所以他非常反感,称之为“贱儒”。总之,扫清天象与星占、相貌与相术间的神秘联系,是扫清智性拓展障碍的基础性工作,是重智主义思想的重大进展,而荀子极有力焉。
(三)荀子何以“科学”之顺向重智:礼智对显、辨合符验与物理可知
无论中西,人类自产生以来的世界图景皆为“天人合一”式。只有走出这种认知模式,才能产生客观知识。从逻辑上来讲,斩断联系是让事物客观呈露的前提。荀子天人观斩断了天人间笼统模糊、互渗不分的所谓联系,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于是,天成为“是其所是”的存在,物“是其所是”地展示自身,人从自然中抽离自身以从事纯客观的认知。荀子在认识事物的环节上进行了大量有益的认识论层面的探索。
荀子重智可从其对智与礼的平列、并举、对显中得到不少讯息。荀子是汉赋之祖,《赋》篇杨倞注引或曰:“荀卿所赋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30]荀子所作赋到底有多少,今已不可确考。从今所存对礼、知、云、蚕、箴之赋来看,礼与智为荀子所重者,而云乃自然之物,亦为荀子所重视。在讲到蚕、箴时,结语用蚕理与箴理,可见其所重者为物之理。从《赋》篇以较为通俗的言语对礼与智的对举,足见荀子将智标举为仅次于礼的范畴。有学者注意到,荀子“有8次提到‘智’,479次提到‘知’(其中‘知’‘智’互通的情形超过50次)。”[31]礼是荀子最为核心观念。礼之一字在今本《荀子》中出现342次。④从礼与智出现的频率角度观之,荀子重智并不在重礼之下,可见荀子之重智。
荀子正名论是走向逻辑学的必要步骤。如果说孔子正名主要突出政治层面意涵,所表现还较为笼统的话,荀子正名的领地则进一步扩大,所论更加详细绵密。当然,荀子尚未发展出科目化、规模化的名数之学与逻辑之学,更遑论科学与数学。易言之,荀子仅有此精神而无此落实。但要看到,有此精神才可能有科学。可惜的是,荀子学脉一直隐而不彰,未能扩而充之、张而大之。此非荀子之过。这构成了荀子研究中一条极为重要且必要的线索。
另外,荀子发展出了一套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辨合符验论。台湾学者王晓波认为,《韩非子•显学》中“验之以物,参之以人”是早于培根的实验论,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中国哲学除了心性论、工夫论之外,还有一个不绝如缕而被湮没不彰的科学“参验论”的传统[32]。若论到“参验论”,荀子的征验、符验思想比比皆是。关于取人、用人,荀子云,“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33]关于正名参验,荀子曰,“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34],“验之所缘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调”,“验之名约”[35],“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36],“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37]作为韩非的老师,荀子辨合符验论无论是理论的运用范围、还是系统性、缜密度皆远非其徒所能比。
荀子的“人贵有辨”内在地蕴示了“天人之分”与“人物之别”。他将存在分为三层,一是天道,一是物道(或者称之为地道),一是人道。在荀子看来,天道、物道与人道三者包含着天、地、人、物分别。“道无不明”,道涵盖一切。在道物关系中,人“可以知物之理”。“物之理”与“物之所以成”是道物关系中隶属于物的背后本质与规律。圣人“辨乎万物之情性”,不失“万物之情”,能了解万物之真实情状。由此,“圣人不求知天”从此获得了完美的解释。不求知天只是圣人措意于人道的表现,并非世人皆不求知天,而是知天之主体另有所属。
人群分工是荀子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点。荀子立言多从管理层的宏观角度,而非具体的职业角度而发。视野与立场决定了其立论论点。荀子多站在“君子”“圣王”角度谈及治国理政问题,而对具体“有司”立场无形之中被遮蔽了。他只是从宏观框架进行设计,至于中观与微观,那就留待“有司”具体执掌之。所以荀子说,“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也,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38]他认为,圣人不需要知“所以然”,只要“用其材”即可。圣人专攻人道而非天道与物道,属政治家与管理者,具体的百官技艺人员则专攻物道,属专业技术人员。正所谓各守其职,各正其位,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在职业分工基础上,进而才能实现物畜而制、制而用之、应时而使、骋能而化、理物勿失、有物以成。
(四)荀子重智为人文理性
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固然相当紧密,但其并非科学理性而仍属人文理性阶段。何以言之?且以天道观念演进为例观之。李涤生认为,“古代天道观念,约有三变:由宗教的天,而为道德的天(义理的天),由道德的天,而为自然的天(物质的天)。”[39]天道观念演进逻辑正是沿着由宗教神性、人文理性、科学理性三阶段而转进。宗教神性在孔子与孟子那里比较显明,虽然他们业已具有了一定的人文理性。而荀子则将人文理性发展到了先秦最高阶段,乃至后世亦难有其比。如徐复观先生认为,“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由周初所开始的从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彻底完成。”[40]“完全成熟”与“彻底完成”八个字来总结荀子的意义,评价不为不高,意义不为不大。从整个学术思想史脉络中,荀子对人文精神的豁显,对宗教神学的贬抑居功至伟,后世罕见。
人文理性是为理性而无可疑,但其并非科学理性。人文理性更偏于人文而非自然,将思维逻辑的力量与人间体知的温度于一体,具有自身出处进退的张力,所以不能说人文理性即能发展出科学,亦不能说人文理性必不能进于科学理性而发展出科学。正如王恩洋所论荀子言,“故其生平注全力于实用学说,而未注全力于纯理学说。故对名学之堂宇但开其门庭,而未全构其宫室。其未竟之绪,竟亦无人继续之,殊可惜也!”[41]有堂宇而后方能有宫室,其规模已初具,继续之、广大之,开出科学亦在情理之中,不过需要曲折转进而已。不可由此苛求古人,进而否定荀子走向科学的可能倾向。
荀子之时,最为迫切之问题是政治一统问题而非科学之事。荀子“他没有征服自然的雄心,只是利用自然而已。”[42]也就是说,荀子处于前科学时代,其时代性已经决定了不可能有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在宗教神话尚处于社会一般信仰之时,荀子对其祛魅,已经足够理性。荀子在周文疲弊(牟宗三先生语)时代起文教、兴礼治,其智性的基本走向是人文领域而非自然领域。从其理论原点处便可见其非求真科学家心态而是一求善的政治家心态,是经验主义为主而缺乏唯理主义色彩。荀子思想虽非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其作为前科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已经做得足够好,若扩而大之,则有发展出科学之绝大可能性。
结语
荀子处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由盛大而衰微乃至行将结束的关键时期,其思想成熟于稷下学宫这一历史、文化、学术大舞台。他长期居于稷下学宫,在这一重要百家争鸣场所批判诸子、熔铸百家,淬炼而成重要的理论成果。荀子学术的一个显明的特征是特别重视概念的梳理与搭建,彰显其理智主义的思想品格。令人叹惜的是,荀子之思路为中国传统所贬抑,但当近代中国受尽西人欺凌之时,不少学人转向荀学找寻资源以期裨益于华族。当今时代疏通中西文化脉络,荀子仍为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思想资源。实事求是地讲,荀子与科学的关系并不直接,但因荀子之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不但不矛盾且非常顺适,故亦可由其思想委曲地走向科学一途。当今的荀学研究当走出尊孟绌荀、曲荀就孟的思想窠臼,接续近代荀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着力显发其智性,以真正厘清传统思想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此对现实当有补偏救弊之益。
注释:
①关于此方面的最新讨论,可参见杨泽波:《性恶论的根本困难——从“道德动力学”角度审视荀子学理的内在不足》,载《管子学刊》,2021年第4期,第5-12页。
②当然,荀子天人观可做多方面解读。如东方朔将《天论》篇还原为一篇政治哲学文献。但不可否认《天论》可作多层次、多角度解读。参见东方朔:《荀子<天论>篇新释》,载《哲学动态》,2017年第5期,第36-43页。
③关于礼义之统的说法,《荀子·不苟》云,“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另外,《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参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20页)。司马迁显然是以“明礼义之统纪”一语来评述荀子。因此之故,研究者多以“礼义之统”来评述荀子思想之大端。
④据荀子研究专家佐藤将之统计,礼字在今本《荀子》中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42次(不含篇名)。参阅佐藤将之:《参于天地之治:荀子礼治政治思想的起源与构造》,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第324页。
参考文献:
[1]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姚海涛.文明接榫与文化疏通:王恩洋荀学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25-32.
[3][7][8][25][26][27]牟宗三.名家与荀子[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218-219,213,193,193,214,214.
[4][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33.
[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6.
[9]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46-85.
[10][美]成中英.荀子:统摄天人之道的系统哲学家[J].齐鲁学刊,2018,(1),5-16.
[11]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9:91.
[12][15][17][30][33][34][35][36][37][38](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356,363,310,457,236,407,408,499,426,229.
[13](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9.
[14][宋]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16]姚海涛.解蔽祛魅与安顿重塑:荀子天人观新诠[J].邯郸学院学报,2022,32(3):5-15.
[18]陈大齐.荀子学说[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25.
[19][41]王恩洋.王恩洋先生论著集·荀子学案(第八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742,710.
[20]鲍国顺.荀子学说析论[M].台北:华正书局,1984:6.
[2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8:233.
[22]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589.
[23]韦政通.先秦七大哲学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38.
[24]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16-217.
[28](汉)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3917.
[2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3.
[31]刘延福.荀子文艺思想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202-203.
[32]王晓波.道与法:法家思想和黄老哲学解析[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xiii.
[39][42]李涤生.荀子集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361,361.
[40]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1.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