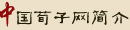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姚海涛】《吕氏春秋》荀学因子探微
作者:姚海涛(青岛城市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原载于 《中国思想史研究》2023年第1辑
摘 要:《吕氏春秋》存有不少荀学因子,此向为学界所忽略。从《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来看,与《荀子》一书在当时广宣流布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从二书相关联的层面来看,在《荀子》普及传播的战国末期,《荀子》成为《吕氏春秋》编撰素材与参照文本的可能性极大。而从《吕氏春秋》文本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观之,其当与齐国稷下学宫乃至荀子有相当大的关联。进一步言之,《吕氏春秋》作者群体甚至可能有荀子弟子。从《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及其表现来看,二书同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有兼容并包、批判熔铸的理论特色,存在用语极类者若干,用典之同者亦不在少数,而思想大端之同者尤其值得重视。二书思想大端之同者,约略有天与人、义与利、古与今、因与假、染与渐等多个层面。探析《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对于正确认知二书间的复杂关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吕氏春秋》;《荀子》;荀学;探微
引言
若从时间先后观之,《吕氏春秋》与《荀子》二书自然是《荀》先而《吕》后,断无可疑。若从思想脉络观之,二书间的隐秘思想脉络则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学者们曾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为二书的关系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结论不一,有些立论亦未确当,也给《吕氏春秋》与《荀子》关系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扰。于是,理清二者关系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话题。
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大作对《吕氏春秋》与《荀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他将二书置于后周鲁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认为《荀子》之于《吕氏春秋》并不存在直接影响。其共通之处可能仅仅与二者共同的稷下学思想背景有关,因共享了稷下思想之故。他根据《史记》中的一些材料提出,《荀子》在《吕氏春秋》成书方面有着某种刺激作用,仅此而已。
二者由于相近的历史场景,所以产生了某些共同的问题意识,由此导致二者有着共通的思想观念。这一观点与之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有着极大不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佐藤的研究立足于后周鲁时代的宏阔背景,且引入稷下学术的共通场景与问题意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其二书并不存在直接影响的结论确值得商榷。《吕氏春秋》与《荀子》二书出现的时间距离如此之近,难道思想距离却会远吗?二书间关系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些问题显然需要重新予以审视,以给二书关系以适当定位。
一、《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与作品性质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策划的一部集体撰作之书。关于《吕氏春秋》创作动机,自然主要当从策划人吕不韦身上找寻。概括学界关于《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与作品性质的看法,大约有以下三点。
其一,“耻以贵显”说。南宋学者黄震认为,《吕氏春秋》是“耻以贵显”而作,由于受到战国四公子及《荀子》书的刺激,“窃名《春秋》”之作。最早指出《荀子》在《吕氏春秋》成书过程中起到刺激作用的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从司马迁的描述可以读出,诸侯国所养辩士较多,吕不韦受到战国四公子养士之风的影响,认为强秦亦当致士、养士,故其所招致之士竟达到三千人之众。这是第一重刺激。战国养士之风的形成主要出于列国雄主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士主要充当智囊团的角色。从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到战国中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再到战国晚期吕不韦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可以得出“学术中心即是政治中心”的结论。这种学术与政治的联姻,成就了百家争鸣的盛大场景,催生出了灿烂辉煌的思想成果。
荀子“著书布天下”则给了吕不韦第二重刺激。于是在吕不韦策划下,由其门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为了炫耀其书之精审,他竟于咸阳门悬赏一字千金。从这一系列操作来看,吕不韦著书的政治动机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其炫耀、卖弄等非政治的商业炒作。显然地,这与吕不韦彼时的丞相角色与政治背景完全不符。
到底是何种原因让吕不韦下决心编写一部以“吕氏”和“春秋”命名的书呢?提到“春秋”,令人马上会想到孔子的《春秋》。冯友兰在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所作的序中说,“然此书不名曰‘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故此书虽非子部之要籍,而实乃史家之宝库也”。吕不韦本人的看法固然重要,但后人的看法可能更加重要。之所以以“春秋”命名此书,当然并不纯粹是将其视为一部历史类或思想类的书,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考量。
其二,政治教化、政治阴谋说。此说认为,《吕氏春秋》是政治性著作,是为了教化始皇帝,甚至为了吕氏篡位夺权所做的思想准备。郭沫若认为,吕不韦与嬴政有着深层次的矛盾。吕不韦虽不一定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但当有着经天纬地、为万世立仪的雄心。《吕氏春秋》的编撰“决不会仅如司马迁所说,只是出于想同列国的四公子比赛比赛的那种虚荣心理的”。
他认为,全书在编制上相当拙劣,“含有极大的政治上的意义”。另,郭沫若推测秦始皇作为大独裁者可能早有表征,吕不韦之所以将《吕氏春秋》赶着在秦始皇八年作出,是为了矫正其施政偏向,为了说教。史学家杨宽与郭沫若观点相类似,他认为,吕不韦之所以在公元前241年把《吕氏春秋》以“一字千金”的高调出场方式公之于众,“是想在秦始皇亲理政务前,使自己的学说定于一尊,使秦始皇成为他的学说的实践者,从而维持其原有的地位和权势”。
钱穆先生的思考则走得更远,关于一字千金之事,钱穆说,“余疑此乃吕家宾客借此书以收揽众誉,买天下之人心。俨以一家《春秋》,托新王之法,而归诸吕氏。如昔日晋之魏,齐之田。为之宾客舍人者,未尝不有取秦而代之意。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必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确实具有政治上的考量,至于有无篡位夺权的阴谋此不可得知。从后来的历史看,吕不韦并没有达到目的,且将自己性命葬送。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主张用法家治国,而拒绝采用《吕氏春秋》儒道交融的治国方式。历史的吊诡是,《吕氏春秋》因政治而生,后来却成为了学术名作,成为荟萃儒道墨诸家的一次学术融合。虽出自众手,却与《荀子》一样,成为汇聚百家学术的总结式著作。
其三,学术杂家、思想集成说。从《吕氏春秋》在思想史上的实际意义来看,学术意义压倒了政治意义。正是高诱所谓“寻绎此书,大出诸子之右”。从撰作主体来说,属于学术队伍从事的政治撰作。学术为政治服务,在战国末年尤其如此。从《吕氏春秋》中的理智之弘扬(郭沫若语)来看,绝非一时头脑发热而作,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长期谋划之作。时至今日,定位《吕氏春秋》为学术作品的争议不大。而关于其是兼容诸子之说的学术性著作,抑或是杂家代表性作品,则存在较大争议。自《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以来,《吕氏春秋》杂家之说似不可动摇。此书虽说有一个统一的策划人吕不韦,但由于出于众手,其在逻辑性与系统性方面大打折扣,难怪乎后人视之为杂家。此论理据充分,不可轻易推翻。
《吕氏春秋》创作动机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湮灭在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由此导致对此书的性质有了不同解读。《荀子》是《吕氏春秋》在形成过程中绕不开的一部典籍,探讨二者间的关联性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二、《吕氏春秋》与《荀子》相关联的几个层面
《吕氏春秋》与《荀子》的关联度到底如何?如上所言,据《史记》,《吕氏春秋》受到《荀子》的刺激而编著,所以说,二书的关联自撰作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
其一,在当时《荀子》已经遍布天下的情况下,《吕氏春秋》撰作者大概率对此书比较熟悉,甚至编撰小组存有此书,并将之作为编撰素材与参照文本。因为彼时,荀子与《荀子》的学术影响力已经很大,所谓“著书遍天下”。荀子曾入秦与昭王、应侯有过深入交流,其弟子李斯在秦国有一定地位,诸多因素使得《荀子》在秦国的传播率必然较高。
徐复观曾对《吕氏春秋》作过系统研究,认为此书是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随之明确指出,其“采用了他人的思想而未出其名者更多,有如孟子、荀子即其一例”。依徐复观,《吕氏春秋》既没有出现荀子之名,亦没有出现今本《荀子》语句,但是该书仍然化用甚至袭用了荀子思想。
《吕氏春秋》为何没有出现荀子?一则,从编撰者个人角度看,若是从稷下学宫出走至吕不韦麾下的学者,可能因自身或师传与荀子有思想过节,而有意忽略之。在《吕氏春秋》中,连子华子都出现多次,而在当时“著书遍天下”,大名鼎鼎的荀子没有出现,显然有些不合常理。二则,从策划者角度看,吕不韦出于让《吕氏春秋》与《荀子》相较量的个人目的,而在下达撰作任务之时,可能有意避开荀子,作了限制荀子入书的硬性要求。果如上所言,则能很好地解释《吕氏春秋》为何没有出现荀子,没有直接引用《荀子》的语句。当然,没有直接出现,并不表示没有间接出现,也不代表没有实质性的思想性影响,更不代表没有荀学因子。
其二,从《吕氏春秋》文本所反映的具体内容观之,其当与齐国稷下学宫乃至荀子有相当大的关联。从司马迁“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的表述来看,吕不韦编撰组中的门客既多,故“人人著所闻”。既然是“著所闻”,其所闻之内容很大一部分必成为今本《吕氏春秋》的内容。而《吕氏春秋》所用典故所涉齐国人物,如管仲、齐王及稷下诸子者较多。如《报更》与《知士》论及静郭君与齐宣王事,孟尝君与齐威王事,亦涉及稷下学宫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为剂貌辨,一为淳于髡。此外,其所提及的稷下诸子还有儿说、尹文、慎到、田骈等。
《吕氏春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人物姓名、典故,还有其差异化较大的思想。而这绝非普通作者所能知悉,所谓非熟知齐国与稷下学宫者不能道也。而齐国重要君臣、稷下人物之隐秘典故,非具有一定社会地位,非久居齐国,亦不能详知也。从事此部分撰作的门客即便非齐人,必有居齐之经验,甚至是曾居于稷下学宫中的士人。可见,《吕氏春秋》作者团队有稷下学宫中游学之士的可能性极大。一个极为可能的推测是,随着稷下学宫的衰落与吕氏门客力量的崛起,不少学宫学者由齐入秦,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参与到《吕氏春秋》编撰队伍之中,将稷下学宫的兼容并包学风、人物典故、学术思想以及齐国君臣从政经验教训等写入书中流传后世。
另,按高诱《吕氏春秋序》的说法,“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其中的“儒书”一词似乎明示出了《吕氏春秋》与儒家间的密切关联。实则不然。按梁玉绳,“儒书”当为“儒士”之讹。需要注意的是,先秦之时,儒不为儒家之专名,而是有学问之人的总称。
胡适《说儒》曾提出,老子是正统老儒,孔老本一家。若将此处“儒书”“儒士”认定为儒家,就难以解释为何《吕氏春秋》中不主儒家而出现杂家的面向。所以,此处的“儒”当采其广义而非专名。如刘向曾将韩非视为“名儒”,正是此意。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编撰团队的人员组成必然具有杂而不纯的性质。这一博杂撰作团队之能构成,稷下学宫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来源。荀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最为老师,其门徒众多,无论是从稷下学宫还是从社会渠道,荀子弟子都极有可能加入撰作团队。
其三,《吕氏春秋》作者中可能有荀子弟子。余宗发认为:“由于《吕氏春秋》成书之时,距荀卿入秦不久,而荀卿又仍然是当时学术界的长者,所以在《吕氏春秋》书中出现了鲜明的荀派儒家思想学说的色彩。”《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41年,而荀子入秦当早于此年。据学者考证,荀子入秦为公元前262年。荀子曾入秦与昭王、应侯对秦国地理风貌、人情风俗、官员设置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并给予了“形胜”“古之民”“古之吏”“古之朝”,“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的高度评价。结合荀子的思想品格,此评价当非恭维之语,而是真实感想。荀子入秦答问对于儒学、荀学在秦国的传播无疑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加之荀子弟子李斯在秦国从廷尉干起直到后来的丞相尊位,这无疑有利于荀子思想在秦国乃至各诸侯国扩大影响。
依郭沫若之见,吕不韦入秦与荀子约略同时。吕不韦可能见过,或者师事过荀子——“即使不韦不曾见过或师事过荀子,而荀子的意见经由弟子李斯间接传到,那可是毫无问题的”。果如是,则主编吕不韦本身就是荀子弟子或“再传弟子”。徐复观认为,《吕氏春秋》“可能受了荀子学说的影响,并开汉儒重师法的先河”。而有学者则认为编者中有不少是荀子弟子,李斯的嫌疑最大。
钱穆从战国晚期学者间的意态,有将自己侍奉的主子奉承为帝王之举,如荀卿弟子颂其师为“呜呼,贤哉!宜为帝王”便为实例,由此推出,“李斯入秦,为吕不韦舍人,吕览之书,斯亦当预,彼辈推尊不韦,谓其宜为帝王,夫岂不可。”杨宽则直接认为,“是时李斯为吕不韦之舍人,必参与其事。”果如是,此种关联不可谓不深矣。至于李斯是否参与《吕氏春秋》编撰,了无证据。胡适推测道,“《吕氏春秋》也许有李斯的手笔,这虽是一种臆测……”云云。而佐藤将之认为,对于吕不韦来说,李斯的分量显然不够,因此并不认可李斯参与撰事。李斯虽然是学界所推测的参与编撰重要嫌疑人,但证据不足,只能阙如。
刘文典在注《吕氏春秋•劝学》“圣人生于疾学”时云,“‘疾’当训‘力’,‘疾学’犹‘力学’也。《荀子》书中‘疾’皆训‘力’,《吕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故用字多与《荀子》同。《尊师篇》‘疾讽诵’注:‘疾,力’,是其谊矣。”《吕氏春秋》“用字多与《荀子》同”,此固然可以构成其与《荀子》间密切联系的重要证据,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吕氏春秋》作者多荀子弟子。”因为《荀子》书当时遍布天下,即使不是其门下弟子,亦不免有引《荀子》为同道者读其书、化用其语。所以,荀子弟子是否参与《吕氏春秋》编撰证据仍然不足。
由上可见,《吕氏春秋》与《荀子》关联度的建立迄今尚未有切实可靠的历史证据。历史证据固然重要,思想证据也非常重要。若从思想传承角度言之,《吕氏春秋》与《荀子》的内在关联不可忽视。这种关联或潜隐或明显,可名之为《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在历史证据不能获得的情况下,从思想证据的角度透视《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成为唯一可行的路径。
三、《吕氏春秋》荀学因子及其表现
(一)理论特色: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兼容并包、批判熔铸
《吕氏春秋》虽没有直引《荀子》,但二书在理论特色、行文句式、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不少相类似之处。从二者成书的先后可推知,只能是《吕氏春秋》借鉴了《荀子》,而非相反。如此,可构成《吕氏春秋》与《荀子》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吕氏春秋》荀学因子由是而显。从《吕氏春秋》与《荀子》二书对学术与政治的先后关系处理上来看,《荀子》基本上是以学术在先,政治在后,以学术疗救政治的诸子学理路展开论述。而《吕氏春秋》则走了一条政治在先,学术辅助政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学理路,甚至可以说其以学术与政治的高度同步性化解了二者先后这一棘手的问题。究其原因,这与二书的撰作主体一为思想家荀子,一为政治家吕不韦紧密相关。以今日眼光观之,二书均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吕氏春秋》与《荀子》均具有兼容并包、批判熔铸的理论特色,具有内在思想与方法的一致性。荀子作为儒家人物,思想上以儒为主,而批判兼摄他家,让《荀子》染上了深厚的批判熔铸色彩。所以研究者对荀子的思想归属有着各种猜测,如认为其是法家、黄老道家,甚至是杂家。而《吕氏春秋》则向来有杂家之称。
如《汉书·艺文志》即将其列入杂家。而关于《吕氏春秋》学派归属的争论一直未断。如此书到底是道家为主还是儒家为主等。之所以出现这些争论,皆因《吕氏春秋》以《荀子》为“榜样”而走得更远些罢了,所以从一开始便“显示了它包容天下的思想与知识的野心。”如果说《荀子》的撰作是稷下学派学术争论与融合的初步产物,那么《吕氏春秋》便是融合之后的进一步精耕细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吕氏春秋》比《荀子》更加精妙,而是各自处于不同的思想阶段的进一步延展而已。
二书的同与异交织在一起,不可苛求。《荀子》一书毕竟基本上是荀子一人之著述,在思想架构上自然比不得《吕氏春秋》来得周全,而《吕氏春秋》则是集体智慧之结晶,是共同创作的作品。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吕氏春秋》在思想深度与历史影响方面较之更胜一筹。这些差异性决定了二书的个性价值,也可以看到《荀子》对《吕氏春秋》隐秘的影响。进一步说,与其说这是二书的系列差异,倒不如说这是《吕氏春秋》在对《荀子》一书的潜在式改进。至于改进的成功与否,自然可以见仁见智。
(二)用语极类者
一般地讲,一个作者若没有看另一作者的文字,独立为文,其用语相类似者,只可能出现在不谋而合地引用某经典文本之中,而在那些原创部分决不会出现极其类似的表述。通读《吕氏春秋》与《荀子》,会明显地感受到其用语极其类似的部分不在少数。而从中亦不难看出,《吕氏春秋》对《荀子》的借鉴。此正是《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之重大表现。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现将极其类似者,列表如下,并于表格最右侧一栏,略作说明。
表1:《吕氏春秋》《荀子》类似句
从上表中对二书的不完全统计可见,《吕氏春秋》因袭、改作自《荀子》之句,确实不在少数。此亦可印证《吕氏春秋》中存有的荀学因子。
(三)用典之同者
用语类似足证其前后沿袭,而用典之同亦可作为二书相袭之辅助性证据。《荀子•大略》有“汤旱而祷”之事,主要体现商汤面对旱情祈祷时,对自身从“政不节与”,“使民疾与”,“宫室荣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兴与”六大方面进行了深刻检讨,追问“何以不雨至斯极也!”祈祷虽属祭祀,但正是荀子所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汤旱而祷”是汤面对上天真挚的内心独白与自我剖析,是以“语言”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事件。而《吕氏春秋•顺民》则进行了大量扩充,将汤之祷的地点、过程、结果进行了详细描摹,是在《荀子•大略》基础上的合理想象与升级造作。
“陈蔡绝粮”这一知名典故,分见于《荀子•宥坐》和《吕氏春秋•慎人》。二书用语一致、篇幅相当、大同小异,皆强调士人遇明主的重要性。“魏武侯谋事而当”则分见于《荀子•尧问》和《吕氏春秋•骄恣》,所述故事情节及用语一致,所谈及者为楚庄王因群臣莫能逮而忧国亡事,皆引中蘬(仲虺)之言,所不同者进谏魏武侯者一为吴起,一为李悝。另一处比较明显的用典之同为氐羌之虏不忧系垒(累)而忧死不焚事。《荀子•大略》云,“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则云,“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所不同者仅为《荀子》引为曾元之言,而《吕氏春秋》未言何人之言。以上典故,非熟知《荀子》字句者,不能写得如此相似。
此外,二书所论及古典人物亦颇为接近,同时出现的人物如奚仲、苍颉、后稷、造父等。《吕氏春秋•君守》言,“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荀子•解蔽》亦有仓颉、后稷、奚仲。此外,二书共同书写的还有蜂门、造父、王良等。按说任何两本书论及历史人物相类似并不构成相袭之证据。可《吕氏春秋》与《荀子》所共享的人物并非分散排列,而是连续三个人物皆处于《荀子》书的一段之中。这就不能不大概率地说明,《吕氏春秋》此段的撰者可能看过《荀子》此段,并有意无意袭用之。
(四)思想大端之同者
《吕氏春秋》与《荀子》思想大端存在相同之处。韦政通认为,“(《吕氏春秋》)书中虽没有提到荀卿其人,却保存了他几个重要的论点,如天生人成(《本生》)、圣人生于力学(《劝学》)、人禽之辨在义(《先识览》)等。”韦先生从天人关系、人禽之辨的角度看到二书间的内在思想关联,是为真知灼见。稍嫌不足的是,其并未对二书思想大端之同者展开进一步阐述。若条分缕析地钩稽二书思想大端之同者,至少包括天与人、义与利、古与今、因与假、染与渐诸方面。
1.天与人:人道为天道归宿
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来看,二书对天道与人道展开的具体方式略有差异,但其理论归宿却高度一致。《荀子》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以人间论题为纲,随时、随事而发,没有事先的主线逻辑安排,所以看起来是一部掘发人道而非天道的思想著作。《吕氏春秋》从《序意》来看,虽是黄帝之学的铺展,其从自然之道出发,以十二纪的时空架构论列思想,纲举而目张,属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著作,其最终归宿仍是人道而非天道。
二书同重人道铺展的政治哲学而非天人自然哲学。《吕氏春秋》所云“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以及“始生人者天也”正是荀子“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思想。荀子认为,君道能群,群道四统,其一为“善生养人者也”。君道善群,其一为“群生皆得其命”。君道、群道即圣王之道。而《吕氏春秋》必不能反对之。二书皆以天道为人道之依归,而以人道政治为主旨,确保圣人、天子的至高地位与管理职能。若将天生人成视为荀子思想的一大支柱,则《吕氏春秋》则为踵其后者。
从逻辑上看,《吕氏春秋》明显更加具有体系建构色彩,其将阴阳家的观念与诸子思想进行了揉合、搭建、重塑,回溯到上古天人不分的圆融中去,是任意比附的神秘主义回潮,极大地妨碍了中国思想史的健康发展。而《荀子》则有其一以贯之的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在天与人之间作一明确对分,重心从天上回到人间,则具有初步的科学意义。可惜的是,在后来的思想史发展过程中荀子的地位渐渐被拉低、被无视,中国哲学主流仅注重“仁”的一面,而忽略了“智”的一面。
2.义与利:乐利主义、为民父母、养生主义的政治哲学
《吕氏春秋》与《荀子》的理论归宿是人道,故其强调人群社会的政治哲学。义利之辨是儒家重要命题,义利关系是儒家特重的关系,在儒家政治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二书已经跳出了孟子“何必曰利”的窠臼,不再罕言利而是有了更深入地认知。《吕氏春秋》提出,“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不利之利属“乐利主义的政治学说。”而荀子早就指出,“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
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荀子将利按严格的逻辑关系分为不利而利、利而后利、利而不利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对应危国家、保社稷、取天下三大不同效果。利而不利,利百姓而不取利于百姓,这就是以百姓之利为利的乐利主义(或称之为爱利主义)思想体现。
《吕氏春秋·贵公》所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与《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有着较高的思想亲缘性。立君为民思想的集中表达是“为民父母”之说。“为民父母”这一打着深深儒家烙印的思想,既是《荀子》非常重视者,又在《吕氏春秋》的《序意》《不屈》二篇出现。《序意》借黄帝诲颛顼之口说出了“为民父母”的政治哲学。《不屈》则云,“《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
《荀子·礼论》则道,“《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吕氏春秋·不屈》与《荀子·礼论》所云简直如出一辙。二者同引《诗·大雅·泂酌》“恺悌(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语,同云君子为民父母之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意》所言与《荀子》理路一致。《序意》篇云,“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按天圜地方之说,圜者为天,矩者为地,君子效法天地,为民父母。此正与前所言荀子“天生人成”意相合,是儒家式的养育万民之意。
《吕氏春秋》与《荀子》同样重视人欲,正视人欲,引导人欲,注重养生。《吕氏春秋·情欲》认为,“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荀子·礼论》坦言,“人生而有欲。”又言,“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圣人与常人同样具有欲望。常人往往不能以礼导欲而滑向恶,而圣人则能够修节止欲、以礼御欲、以礼制欲。欲望与养生密切相关。
二书在对百姓养生方面,皆有精深见解。此可归属于养生主义政治哲学。《吕氏春秋·本生》“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与《荀子》“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以及“重己役物”的思想完全一致。《吕氏春秋》“养有五道”从养体之道、养目之道、耳之道、养口之道、养志之道五个方面展开,这与《荀子》“礼者,养也”中所列的养口、养鼻、养目、养耳、养体并无多大的不同。另,荀子《正名》有养目、养耳、养口、养体、养形、养乐、养名之说,《修身》《不苟》中又有养心之术、养心莫善于诚之说。
3.古与今:古今一也、审今知古、法后王的历史哲学
古今之辨属历史哲学范畴,是《吕氏春秋》与《荀子》又一共同话题。二书皆成于战国末期,站在古今的转折点上,自然会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古与今作为时间概念来讲,不可分割,同为一体,也就是荀子所谓“古今一也”。《吕氏春秋·长见》明确指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此与荀子“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若合符节。二书对古今一体的感知完全一致,对圣人、先王智通古今的崇敬之情完全一致,皆由古今之辨生出了以今知古、以古持今、贯通古今的方法论。
古今之辨中的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是古今之辨论题中不可回避的方法论问题。从总体上来讲,古今一体,“类不悖,虽久同理”,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则由于“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法古不若法今,法先王不若法后王。二书在法后王方面也达到了高度的思想一致。《吕氏春秋·察今》指出,“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一则,人或损或益,先王之法本来面貌已失,如何可法?二则,古今之法,言异典殊,多不能相通,如何能法?三则,先王之法适用于先王之时,具有时效性,古今变化差异之大,如何法之?由于先王之不尽可法,自然要以近知远、以今知古、察己知人。进而言之,法先王还是后王,这都不是问题,要害是法其所以法,关注法背后的精神与思想,找到确不可易的方法论。
4.因、染与假、渐
观二书,会发现《吕氏春秋》因、染思想与《荀子》假、渐思想间互相融通。《吕氏春秋·顺说》云,“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王念孙指出,“‘际’疑‘登’之讹。”此说甚是。相类似地,《荀子·劝学》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二书用了“顺风”“登高”这样极为类似的语言,表达出了相通的思想:因与假。因,指的是因物乘便、因势利人。假,指的是假借物性以利人。可见,因与假之相契相通。《吕氏春秋·当染》引用墨子所见染丝之叹“故染不可不慎也”而生发“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与《荀子》“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取友善人,不可不慎”,“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等一系列思想完全一致,均表达了环境、学习、师法等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治国观上,二书皆看到了明分、定分之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在军事观上,《吕氏春秋》大量的“义兵”之说与《荀子》“仁义之兵”思想毫无二致。《吕氏春秋·适音》与《荀子·乐论》更是可互相参合,二篇关于乱世之音与治世之音的分别,关于音乐对政治、习俗作用的描述以及在移风易俗、平政化俗发挥的重要作用均可引为同调。
结语
《吕氏春秋》与《荀子》创作时间前后相续,均为先秦与秦转捩之时的集成性思想大作,二书有着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从创作动机、撰作者共同的稷下学背景、思想亲缘诸方面皆可见。《吕氏春秋》作者群体的多元化直接导致了思想博杂的特点,也成就了其兼采众家的思想特色。主编吕不韦有意识的规划与参编者的精心建构,又使得此书成为一包容性极强、结构性极谨严的著作。透过字里行间,可以把捉到其中的荀学因子,嗅到其中的荀学气息。《吕氏春秋》与《荀子》均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具兼容并包、批判熔铸的理论特色,存在不少用语极类者,亦有用典之同者,更有思想大端之同者。可以说,《吕氏春秋》中的荀学因子处处可见,在思想方面存在不少相通之处。明乎此,对于理解二书的关系当大有助益。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