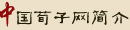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中国先秦史学会荀子研究会
河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邯郸市荀子研究会
协办单位:邯郸学院荀子学院
河北工程大学荀子研究所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赵文化研究所
邯郸市旅游局 兰陵文化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邯郸市荀子中学
运维单位:荀卿庠读书会
怀念李泽厚先生
梁 涛
一
11月2日,李泽厚先生以九十一岁的高龄在美国家中去世,官方讣告称其为“我国著名哲学家”,我想多数人可能更愿意把他看作是思想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风气之先的启蒙者。李先生一生影响了很多人,但对我的影响则是具体的,当年我就是因为读了李先生的著作而走向了思想史研究。今天他离我们而去,悲痛万分,撰此小文以示哀悼。
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当时“文革”遗留下来的思想枷锁已被打破,但大学课堂上所教还是教条化的内容,是李先生的著作打开了一个窗户,使我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有了亲近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我当时反复阅读的著作,其中的《孔子再评价》奠定了我对儒学的初步理解。后来文学黑马激烈批评李先生对传统的温情态度,一时竟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一度对李先生的观点产生过怀疑,这可以说是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要将思想史作为我毕生的研究方向。1990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专业就是思想史。那一年正好所里举办一个思想史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不像现在,学术会议很少,自然是一件大事,而且我得到一个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李泽厚先生将来赴会。于是我又翻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准备着当面向李先生请益。然而一直到会议结束,李先生都没有出现。我听所里老师说,李先生是想来赴会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这样我就错过了与李先生见面的机会,后来我听说李先生去了美国。不知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李先生到了美国,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后,思想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突破和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具震动性的作品。我当时有这个想法十分自然,丝毫没有感到奇怪。
我真正见到李先生要到1999年了,那年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国际儒联举办的会议,每五年一次,会议规模较大,与会学者可能有二三百人,均是国内外研究儒学的名家,其中包括李泽厚先生。我当时在社科院历史所做博士后,也得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与干春松约定,一起去拜访李先生。李先生已经在房间休息,听说我们要来,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我自我介绍说,我硕士、博士都是在西北大学思想所读的,现在社科院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做博后,这两个地方都是侯外庐先生建立的,所以我算是出自侯门了。李先生说,侯外庐先生是马克思学者中最具有原创力的,至今不过时。我说您对我的影响更大,我本科阶段主要读你的书,硕士阶段才认真读侯先生的书,所以我研究思想史是受您的影响。李先生发出爽朗的笑声,但他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你们年轻学者对我是怎么看啊?还读我的书吗?对李先生的著作,我当然是一直重视的,但主要限于思想史方面,尤其是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今天写文章还会引用。但我读博士时,兴趣已经转移到港台新儒家,更多时间是在读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的著作,李先生从生活实践、情感积淀解读传统,与新儒家高扬心性主体、贯通天道性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子,但当时更吸引我的已是徐、牟了,而且他们的著作更为系统,更注重传统思想的内在逻辑。李先生由于比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并不是从研究中国哲学或思想得出的,而是他从外部借鉴来的,所以如何用他的情本体、吃饭哲学合理地解读传统思想还是有待探索和完善的。所以我说,您的著作我们当然是非常重视的,但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影响也很大,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学者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接着问,您对牟宗三先生如何评价呢?李先生斩钉截铁地回答:高水平!很有造诣!说明李先生对牟先生是十分肯定的。
李先生和牟先生都是我对学术成长产生深远影响的前辈学者,而且他们二人都关注康德,通过康德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进而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但他们一个往下拉,一个往上升,价值取向是很不一样的。李先生把康德拉向形而下,用他的话说,是变先验为经验。他真正重视的还是来自马克思的工具本体,指人能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实践,他之所以主张“西体中用”,就是因为近代科学包括科技发明主要是来自西方,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而不同民族在生产实践中有不同的心理积淀,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不必唯西方马首是瞻,所以又要“中用”。所以李先生的哲学思考,首先是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同时又肯定文化传统的价值,这与八十年代激烈的反传统风气有所不同,文学黑马《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之所以对李先生展开批评,原因就在这里。牟先生则是利用康德哲学把儒家的心性之学纯粹化、精神化,通过赋予人“智的直觉”这一属于上帝的天资,贯通天道与性命,建构起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并试图超越康德的神学形上学。牟先生的这一努力,如学者所说,主要是在儒家客观存在的社会教化体系被一扫而空之后,必须通过一种孤悬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去论证儒家依然具有合法性意义,进而承担起儒家精神在特殊历史关头存亡绝续的使命,具有很深的悲情意识和豪迈情怀。两位先生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问题不同,哲学的选择也不同。尽管今天我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已经与他们有所不同,甚至存在根本分歧,但我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步步走过来的,这就是学术的薪火相传吧!李先生的著作使我这个生活在十三朝古都、周秦汉唐故地的年轻人,在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同时,开始关注并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古老的文化还有没有生命力?能否继续换发出打动人心的力量?能否像历史上那样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一个精神上的信仰力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实际取决于我们。传统或许并不能决定我们,但我们的选择则决定了传统的未来。
那次会议上,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会议结束后,李泽厚先生与几位学者进入餐厅就近入座。这时有服务员过来说:先生,请往里面坐,这张桌子有预留了。没有想到李先生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问道:我不能坐在这里吗?不允许坐这里吗?他站起身来对着在座的人说:我们就坐这里,大家动筷子。说着拿起一瓶啤酒往桌子上使劲一顿,啤酒沫顿时从瓶中溅了出来。过了一会,李先生冷静下来,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是不是有点失礼啊?李先生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师伯何兆武先生解围说:没有。他赶我们不对,是他们失礼。那天我正好在场,目睹了这一幕。我知道那位服务员并没有恶意,这种会议规模较大,人数众多,除学者外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会议一般会安排学者在餐厅里面就坐,门口的几桌往往是留给工作人员的。但他的直率表达,却刺激到了李先生。这也使我意识到,虽然离开国内多年,但李先生的心中还有一股郁闷之情,这或许与他的遭遇和经历有关,只是我们外人无从了解罢了。

二
我1998年到社科院历史所做博后,那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时成为显学,我的博士后报告也定为《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李泽厚先生虽然不是出土文献研究的专家,但由于他的影响力,他的看法还是很受学界关注,他撰写的《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成为当时被广泛引用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对当时学术界将郭店儒简定位于“孔孟之间”,归于思孟学派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总起来看,竹简各篇年代不一,内容兼容并包,参差不齐,并不完全一致”,“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我知道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曾专列一章讨论思孟学派问题,后来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也有一节“思孟学派考辩”,但观点与侯外庐先生相反,否认思孟学派的存在。我印象中李泽厚先生曾参与了任继愈先生主编的白皮本的《中国哲学史》,或许他的观点受到任继愈先生的影响。当时我已经写了一篇《思孟学派考述》,发表在《中国哲学史》上,看到李先生的观点后,便一直想做出回应。后来在哈佛燕京学社“思孟工作坊”上,也有一位学者指出我那篇文章有疏漏,于是我决定把那篇文章重新写一遍。那时已经有了数据库,我用“四库全书”软件将“思孟”“子思孟子”“子思”等关键词逐一做了检索,然后按图索骥,将索引到的文字仔细阅读,梳理出基本的线索,又在原作的基础上补充了宋明时期思孟学派的材料。由于是第一次使用E考据,加之资料繁多,这一稿前后又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收入《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的实际是这一稿。2008年中旬拙作出版,大概下半年的一天早上,还在沉睡的我被电话叫醒。我拿起电话,里面传来李先生的声音:“你是梁涛先生吗?我是李泽厚。你的大作我拜读了,思孟学派的问题,你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被你说服了。不过还有一些问题,我的看法与你不同。”之后的一段时间,李先生不时从美国打来电话,往往是他读了一两章便与我来讨论,或赞同或质疑。由于时差的原因,李先生打电话的晚上,是我这里的早上。大约过了半个月吧,李先生终于把拙作看完了。我最后一章是“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实际是提出统合孟荀的问题,李先生评论说很有意思。
那些年李泽厚先生每年秋天都要回北京住一段时间,2009年他回北京前与我联系,约定见面详聊。李先生原来住在皂君庙社科院家属院,与庞朴、黄宣民先生一个院子,后来搬到国家美术馆附近的一个家属院里。那天我带了两位研究生,打车来到李先生所给的地址,我们在寻找楼门时,遇到一位女士,她说:“你们是来找李泽厚的吧?昨天傍晚我在院子里看到李泽厚和他老伴了。”看来李先生还是被大家惦念着,只要他回来,拜访的人仍是络绎不绝。见到李先生,我将这件事告诉他,李先生摆摆手说:我都是悄悄来,悄悄走,你们是我今年见的第一批客人。李先生的房子好像只有一室一厅,客厅大概只有十平方米左右,但很整洁,墙边摆了一个明式茶几,上面挂着冯友兰先生书写的一幅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皂君庙庞朴、黄宣民先生的家我经常去,李先生的房子应该与其相似,与那里相比,这里是小了不少。李先生解释说,他是space for distance,这里虽然面积小,但环境好,从窗户望去就能看到美术馆,每年回来可以去看展览,会见朋友也方便。
我来见李先生前就想到要请他去人大做一次报告,李先生离开大陆多年,仍笔耕不辍,不断著作问世,且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人大国学院开设有“《论语》研读”的课程,他的《论语今读》就是重要的参考书。可是当我提出邀请时,李先生却说,你不知道我的“三不”吗?不接受采访、不参加会议、不发表演讲。所以恕不能接受邀请了。我真不知李先生还有这样一个“三不”规定,但不好勉强,只好说改天来人大国学馆坐坐,我邀请几位研究思想史、儒学的年轻学者,大家一起聊聊天,不算是会议,也不算是演讲,这样如何呢?李先生总算答应了,但等我后来联系他时,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所以计划中的人大聚会最终还是没有搞成。
李先生问我最近做什么?我说写完思孟学派后,我转而研究荀子了。李先生听后兴奋地说:荀子重要啊!我一直是重视荀子的。孟子也重要,但荀子的影响和作用更大。我知道李先生不是从儒学史来讲的,从儒学的发展来看,孟子后来被尊为亚圣,其著作也完成由子入经的转变,而荀子后来不仅未能列入道统,甚至被罢黜孔庙。今天我们游览曲阜孔庙,不仅大成殿四配、十二贤中不见荀子的身影,东西两庑156位儒家先贤也未有荀子的牌位,荀子的处境不可谓不悲惨,其地位当然不可以与居于大成殿四配之中的孟子相提并论。但李先生说的是历史中的实际影响,他认为从这一点看,荀子的影响显然更大,也更为重要,这与谭嗣同等人的看法实际是一致的。我说自己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想利用新材料在荀子研究上有所突破。李先生问:有这方面的出土材料吗?我说直接相关的材料似乎还没有,但我同意您的判断,不应该将郭店儒简笼统归为思孟学派,里面也有与荀子相关的内容。另外,子思的思想也不是如我们以前认为的,只影响了孟子而与荀子无关,实际情况是子思既影响了孟子,也影响到以后的荀子。这点我在那本书中已有详细论述,学界也已认可。我想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讨,而且据我所知,还有一些竹简会陆续公布,希望会发现与荀子相关的材料吧。李先生说,这个课题很有价值,值得探讨。
由于李先生有很严重的失眠,昨天刚回到国内,今天中午因为我们要来,没有休息好。李先生说:我左等你们不来,右等你们不来,一中午就在等待中过去了。其实我们本来可以早点到的,就是想着李先生可能要午休,所以有意晚到了一会,没有想到却给李先生造成了困扰。于是我们起身告辞,李先生送我们到门口,临别时说:我很欣赏你书中的一句话。我停下身子,想知道是哪句话?“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记住。”李先生念出的是我书中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我看到李先生伸出大拇指对我的学生说:你们老师,这样的!
从李先生家里出来,我多少有些感慨。我知道李先生与我的后记产生共鸣,多少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但这样的共鸣其实是不恰当的。我说的“自我放逐”是感慨于学术界的考核体系,明显不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所以有时步子慢一点,职称评晚一点,从长远来看未尝不是好事。但李先生是成名已久的学者,甚至已过了学术的高峰期,有什么必要自我放逐呢?如果他把“三不”看作是一种自我放逐的话,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学生说,李泽厚先生应该积极一些,不要人为地将自己与学术界隔离起来。如果能多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对他自己如何暂且不论,对学术界肯定是大有裨益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李先生怎么考虑,我就不得而知了。

三
以后的几年,我与李先生一直保持联系,李先生回到国内也会约我去聊聊。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应该是2014年首届“致敬国学”的启动仪式,那次活动来了不少著名学者,也有不少媒体记者。活动开始前,组织者安排学者在一个大的休息室里休息,很多记者顺便进来采访。这时有人喊了一声:李泽厚先生来了!只见陈明兄陪着李先生阔步走进休息室,在场的记者哗啦一下围了上去,有的甚至将正在采访的学者晾在了一旁。我就看到一位著名学者面露尴尬之色,但不由感叹,时隔这么多年,李先生的影响还是无人能及。但李先生似乎还在坚守他的“三不”规定,不接受采访,他只客套地说了一句:祝贺致敬国学大典顺利召开。然后就不愿多说了。我与李先生聊了几句,送给他一本我新出版的《儒家道统论新探》。李先生参加完剪彩仪式后,便在陈明的陪同下离去了。之后李先生回来的次数逐渐少了,听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2017年,我没有去打扰他,也没有与他见面。
虽然我与李先生见面次数少了,但一直保持邮件联系,后来又加了微信,联系更方便了。李先生来信往往会问最近又公布了哪些出土材料?我的荀子研究进展如何了?我去信如实汇报,荀子研究有了新的发现,也首先将论文寄给他,请他批评指正。我的《荀子人性论辨正》一文对荀子人性论提出新的解读,认为荀子实际是性恶、心善论者,而非传统所理解的性恶论,以此解决荀子的主体性问题,反驳“大本已坏”的误评。根据是荀子所说“其善者伪”的“伪”并非以往学者所理解的人为,而是指心的思虑活动,其本字应该是郭店简中的“”(上为下心)。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便寄给了李先生,想听听他的意见。我给李先生去信是2015年5月25日,5月27日,李先生用电邮回复了我。
梁涛,你好!
文因目力不济,未及读毕,因近月事烦,先说几句:释“伪”为心为甚好,但与人为并非水火,因人为也必须有心为。要害在于心为(思)何以即善?心也可为恶。我以为心之所以能善并不在先天,不在本就是道德心。如此,则与孟相近(不过孟以情,荀以理即以思、以心而已),而在于学(学礼)。心由学而知礼义才有道德,所以“劝学”乃首务。孟是先验论,荀是经验论,孟是由内而外,荀是由外而内,即由礼而理(心)而道德。尊作于此似不明朗或有矛盾。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我于荀子并无研究,仅供参考。
李。
李先生的回信实际包括以下几点:(1)赞同用“心为”()而不“人为”理解荀子的伪。研究过荀子的都知道,传统上人们是用人为理解荀子所说的伪,这样荀子的重要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便被理解为:人的性是恶的,善却是人为的结果。但这个解读其实是经不住追问的,人为有很多,有善的人为,有恶的人为,还有与善恶无关的人为,也就是中性的人为,人为何以能必然导致善呢?而且一个人性恶,他为什么不听从本性为非作歹,从事恶的人为,反而要通过人为成就善呢?人为的解释没有回答善的动因和根据的问题,是不完备的,这点李先生与我的看法一致。(2)荀子的心是否具有善的动力,能否称为心善?这点李先生的看法与我有分歧。学界传统的看法是荀子虽然也重视心,但其心主要是认知心,能学、能习,但不能做道德判断,尤其不能做道德创造,最多是一种聪明才智。但这种说法同样是经不起追问的,一个人性恶,又有聪明才智,他应该更坏才对,怎么可能会化性起伪,学习礼义,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圣人呢?这是讲不通的。其实荀子的心并非一般的认知心,而是道德智虑心,好善、知善、行善,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这也是荀子反复陈述和强调的,如“人之所恶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荀子·强国》)这里虽然没有点出心字,但所好所恶者显然指心,即所谓“体恭敬而心忠信”(《修身》)。荀子又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非相》)这里的“辨”就是辨是非善恶,显然也是心的能力。荀子还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这里的“义”是生而具有的,西方学者将其翻译为the sense of justice,它是人的族类规定性,是人所独有而禽兽不具有的。正是因为荀子的心能辨、好义,所以即使性恶,依然能追求善、实践善。(3)如果将荀子称为心善,那如何与孟子相区别?这是李先生的疑问。李先生说孟子是先验论,荀子是经验论,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这也是学界固有的看法,不过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疏。我认为荀子的心也有先天的成分,不过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具体的内容,这点他与孟子确实有所不同。孟子的心是“实心”,是有具体内容的,即他所说的四端之心,可以由内而外直接表现为道德行为。荀子的心则是“虚心”,虽然能辨、好义,但只是一种能力,没有具体内容,辨和义的内容要在后天获得。从这一点看,心善更像是语言的能力,人虽然生而具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先验的),但使用语言则需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过程(经验的),心能够善也是如此。另外,李先生说荀子的心可以善,也可以恶,所以不好说心善。其实这也是孟子的特点,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可见孟子的心也存在思和不思的问题,如果不思,一样可以为不善。有学者提出,孟子的心可以分为两层来看,一是日常经验心,可善可恶;二是道德本心,这个是本善的。荀子的心一样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可善可恶的是经验心,可以为善的则是道德智虑心。以上内容我写入《统合孟荀,创新儒学》一文,算是对李先生的回应吧。
我知道,李先生虽然在荀子的问题上仍持传统观点,但他实际是非常重视荀子这一脉的,并想将其纳入儒学的谱系中,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2017年,李先生发表了《举孟旗行荀学》一文,提出“兼祧孟荀”,与我主张的“统合孟荀”不谋而合。于是我在人大国学院组织了“重估道统与统合孟荀”学术研讨会,专门围绕李先生的文章展开讨论。李先生当时在美国,无法赴会,但做了书面发言,委托刘悦笛宣读。与会的杜维明先生回顾了他与李泽厚先生的交往,肯定李先生对重新评价孔子在当时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他的主张提出疑惑:既然举孟旗了,为何又要行荀学?既然要行荀学,为何又要举孟旗?我后来看到李先生在华东师大的一个会议上说,他的观点在人大国学院受到批判。其实是误解,大家还是非常肯定李先生高屋建瓴的卓见的,只是在具体论证上有不同看法而已。
李先生一直关注我的荀学研究,尤其想知道我如何用出土文献研究荀子,这也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直到两年前,我因为清华简《命训》等篇的发现,注意到《逸周书》其实是子夏学派为配合魏文侯的变法活动而编订,其中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作为全书的总纲,与荀子思想存在密切联系,填补了孔荀之间儒学发展的空白。以往受道统论的影响,人们只注意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谱系,而忽略了孔子—子夏—子弓—荀子的线索,后者其实是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围绕这一发现,我先后写了两篇文章,后一篇《孔荀之间——以清华简〈命训〉与〈逸周书〉“三训”为中心》完成后,与以往一样,我将它寄给了李先生。我的电邮如下:
李先生:您好!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孔荀之间》,是利用清华简讨论孔子到荀子思想发展的,知道您非常关注荀学的研究,发给您,请批评指正。谢谢!
祝好!
后学 梁涛即日敬上
我发这封邮件是10月26号,但一星期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收到回复。这让我多少感到一丝不安,按照李先生的习惯,他收到信后,一般都会简单回复一句。11月3号中午,我下课回到办公室,打开微信,准备给李先生发个问候,一则信息突然跃入眼帘:李泽厚先生2日在美国去世。我这才知道李先生已于昨天离我们而去了。听刘悦笛讲,李先生最后几天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么我的电邮应该是一直静静地躺在李先生的邮箱里,而且将永远躺在那里了。
11月7日于九州西雅苑
11月28日删改
Copyright © 2014-2019 www.chinaxunzi.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荀子网运维 电话:13051618021 微信:22993341
有别字、漏字、错误版权问题等请留言或联系编辑
冀ICP备2024075312号-1 邮箱:2299334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