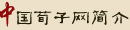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支持计划“新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10XNJ028)前期成果。]*
——论《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
梁 涛
摘要: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记录的是荀子不同时期的看法。根据内容及成书时间的不同,荀子讨论人性论的文字可分为四组,其中《富国》《荣辱》可能为荀子居赵时作品,反映了其前期的人性论思想,其特点是提出了情性-知性说,将情感欲望与材性知能都称为性。一方面认为顺从情性或情感欲望会导致争夺、混乱,因而蕴含有情恶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知性可以做出抉择判断,制作礼义,“知者为之分”,实际是将知性看作善的来源。《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为后来《正名》《性恶》篇中的性-伪说做了理论准备,但又有所区别。一是没有提出明确的性恶观念,二是在性概念的使用上存在含混模糊的地方,不仅将情性、知性都笼统称为性,而且将生而所具的认知能力(能知)与后天的认知结果(所知)也都归为性。后荀子通过对性的两重定义(《正名》),将性主要限定为情性,同时又提出伪的概念,以概括能知和所知,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前期思想中的矛盾。《富国》《荣辱》还没有出现伪概念,是其属于荀子前期思想的反映。
关键词:《富国》 《荣辱》 情性 知性
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将荀子人性论简单理解为性恶,并以性恶来认识、评价荀子的思想。二是否认性恶与荀子的关系,试图对荀子人性论做出重新理解和概括。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荀子》书中有《性恶》一篇,明确提到性恶。另一方面,除《性恶》之外,《荀子》其他各篇均没有性恶的说法,仅《荣辱》篇提到“人之生固小人”。在对人性的态度上,《性恶》与其他各篇也有所不同,存在着“逆性”与“顺性”的差别。将荀子人性论简单理解为性恶,固然有失片面,但完全否认《性恶》与荀子的关系,同样不可取。因此,讨论荀子人性论固然不能只限于《性恶》篇,还应考虑其他相关各篇的内容,但也不能无视《性恶》的存在,将其排除于荀子的思想之外。合理的作法应该是将《荀子》中涉及人性问题的各篇做一系统考察,从而在宏观上对荀子人性论有一整体、全面的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荀子》各篇关于人性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荀子的生平以及《荀子》的成书有一定关系。据《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荀子五十岁以前主要活动于赵国,[ 关于荀子“始游学于齐”,学术界有“年五十”和“年十五”之争,后者的根据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笔者认为荀子“游齐”应为“年五十”,而非“年十五”,胡适、罗根泽、蒋伯潜、龙宇纯、廖名春等对此已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展开。]是在赵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而赵所属的三晋乃法家的发源地,有尊崇法家思想的传统,战国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即赵国人,荀子长期生活于此,不能不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在齐湣王执政末期来到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当时稷下主要流行的是黄老道家思想,《荀子》书中一些明显受到黄老思想影响的作品,可能就完成于这一时期。晚年则退居兰陵,“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兰陵当时虽属于楚国,但历史上则是鲁国的封地,故荀子晚年又受到鲁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荀子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其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其观点存在分歧、变化,有思想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是十分正常的。另外,《荀子》一书与《论语》《孟子》不同,《论语》《孟子》为记言体,是对孔子、孟子生前言行的记录,其成书分别是在孔子去世之后和孟子晚年,是由孔子弟子或孟子与其弟子共同编订。而《荀子》则主要为议论体,各篇都是主题明确、内容相对完整的论文,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在一个时期集中完成的,而是写作于不同时期,有些开始甚至是作为单篇流传的,荀子去世后由其弟子搜集、编订成书。因此,讨论荀子的思想就不能采取一种静态的、非此即彼的认识方法,而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动态的发展中揭示其思想的轨迹,把握荀子人性论的基本主张和特质,并对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原因做出分析和说明。而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对《荀子》相关篇章的写作年代做出考订和说明。
关于《荀子》各篇的写作年代,已有学者做过考证,但在具体结论上存在一定分歧。[ (日)金谷治:《〈荀子〉の文献学的研究》,《日本学士院纪要》1950年,第9卷第1号。里西:《〈荀子〉书重要篇章的写作年代考证》,《哲学研究》1990年增刊。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62页。]就本文的讨论而言,我们将所涉及人性问题的篇章根据年代分为四组。其中,《富国》和《荣辱》为一组,应完成于“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之前,其特点是提出情性-知性说,反映的是荀子前期的人性论主张。《礼论》《正名》《性恶》为一组,《王制》《非相》为另一组,两组文献应该都完成于五十岁游齐之后,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礼论》等篇提出性-伪说,《王制》《非相》则提出了情性-义/辨说,二者均属于荀子中期的思想。《修身》《解蔽》《不苟》为另一组,该组文字可能不是完成于同一时期,而是时间跨度较长,但都是讨论养心或治心问题,构成荀子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其余三组文献则另文讨论。
一、情性、知性、仁性:先秦儒家视域中的人性
人性为何?是善?是恶?亦或其他?千百年来一直是困惑无数哲人的永恒问题,而关于人性的探讨也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从现象上看,人首先是生物性存在,有基本的生理欲望,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生命便无法延续,故“食色,性也”便成为不言而喻的共识。但是另一方面,人又是灵性的,在满足基本欲望的同时又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人不同于禽兽之所在,是人之所为人者,而这些内容往往也被看作是性。故所谓人性实际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既有生物性,也有道德性。而在这两者之间,人既可能屈从情欲,堕落为禽兽,也可能挺身而出,服从道义的召唤。人既可以为君子,也可以为小人;既可以为圣贤,也可以为强盗。这恐怕才是人性在现象界所呈现出来的最为明显也最让人费解的特征所在,而对于这一特征的思考和探讨,便成为儒家人性论的主要内容。至于性善、性恶,不过是对于人性问题并不准确、全面,一种简单化的概括而已。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提出了对人性的看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从孔子生活的时代看,这里的“性”应该是自然人性,指生理欲望;而“习”指积习、习惯,也包括道德品质。故人在生理欲望上是大致相同的,而外在的表现则相差很远,既可以为工匠,也可以为农夫;既可以为君子,也可以为小人。如果说“性相近”可以从上天的赋予来解释的话,那么“习相远”是如何形成的?则无疑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说明的问题。从孔子的论述来看,积习、习惯的养成显然与后天的修习、实践也就是“习”密切有关,而作为修习、实践的习又与学联系在一起,故说“学而时习之”(同上)。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学,不仅指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指学习做人。“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雍也》)这里的学显然已超出一般认知的范围,而是指塑造道德人格,发明道德主体。学离不开知,故孔子谈学也谈知,孔子的知并非一般地指认识外物,而是以“人事”为主要内容,包括“知人”、“知十世”、“知礼”、“知乐”、“知过”、“知言”等,是一种伦理性认知。不过,学或知只是说明如何成为善人、君子,而不能解释为何要成为善人、君子。“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上达者君子,下达者小人。”故人既可以向下堕失,也可以向上提升,而在孔子那里,这种向上提升的力量无疑就是仁了。“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无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过错,而是说仁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代表了人生的正确方向,一旦确立起仁,就可以远离过错了。徐复观先生称仁是“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 徐复观:《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民主评论》1955年6卷6期;又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确乎有见!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同上)。可见,仁比智更根本,只有具有了仁才能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仁在孔子那里是内在的,“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里的“至”,不是由外而至,而是由内而至,是由内而外的显现。从这一点看,仁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性。只不过孔子的仁还需要在后天的实践中进一步扩充、完善,需要经过知的补充,仁与知是联系在一起的,故称“仁且智”。因此孔子所理解的性实际包含了情性和德性,而德性又可分为知性和仁性。人在情性上是大致相同的,但由于仁性、知性的实际表现、运用不同,每个人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习性又相差很远。只不过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孔子对仁、知与性(或心)的关系尚未做出明确说明,所谓情性、仁性、知性还只是蕴含在其思想之中,是其分析人性问题时一种潜在的维度和框架,代表了儒家人性论未来可能具有的发展方向。[ 孔子欲性、仁性、智性的三分法是杨泽波较早提出的,见《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孔子之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提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这里的“性”是自然人性,是情性,而“心”是知心,是道德认知心,而人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在于学,“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李零,第136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故实际延续的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但又心、性分立,将情(欲)归为性,将知(智)归为心。竹简下文又说“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李零,第138页),[ 同上,第138页。]似乎认为仁也属于性,但又不肯定,故用一“或”字。可见竹简实际也涉及到情性、知性、仁性三个方面,但主要讨论的是前两者,并将其分别归于性和心。孟子论性虽然以“性善”著称,但实际也涉及到情性和仁性两个方面。“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属于情性,“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则属于仁性(广义的),故孟子所说的性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是一种双重结构,既有生物性,也有道德性。只不过孟子一句“君子不谓性也”,将情性一笔带过,而主要关注的是仁性,认为应将仁性看作是真正的性,并即心言性,提出了性善说。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论性与孟子有所不同,主要关注的是情性与知性,一方面对孟子轻易放过的情性着力阐发,大书特书,并就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和说明。另一方面又突出知性,对人的道德认知能力做了反省和考察。但就其所讨论的性而言,同样是一种双重结构,而且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实质的联系。这在其早期作品《富国》篇中已明确体现出来。
二、《富国》情性-知性说的提出
《富国》虽然不是专门讨论人性问题,但实际已涉及到情性、知性的问题。
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注:于)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注:患),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注:悬)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万物形体各异而同处宇宙之中,虽无一定之宜,但却可以为人所用,这是必然的。下文“同求”、“同欲”显然指情性而言,而“异道”、“异知”则是知性运用的结果。“可”指人的判断能力,其来自智而不是来自欲,《正名》就将可定义为心的功能。人人都有判断的能力,这没有智愚之分;但判断的结果有对有错,智愚由此得以区分。《荀子·修身》:“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就是以是非判断定义智愚的。故《富国》实际提出了以“欲”、“求”所代表的情性,和以“可”、“知”所代表的知性。“求”与“欲”出于先天的本然,故同;“可”与“知”取决于后天的运用,故异。但《富国》将二者都归为性:“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生”,即性也。不过说“同求”、“同欲”属于性固然没有问题,但若说“异道”、“异知”也属于性则会引起异议,李涤生说:“此文‘生(性)也’,只指‘同求’、‘同欲’说,不包括‘异道’、‘异知’;否则,便不可通。”[ 李涤生:《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196页。]但从荀子的论述来看,显然是将“异道”、“异知”也归为性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知”既指人生而具有的认知能力(能知),也可指认知能力的实际运用(所知),而荀子注意到现实中人的“可”与“知”相差很远,但又没做详细分析,一概笼统称为性。后荀子提出“伪”概念,才对“能知”与“所知”做了区分,将前者归为性,后者归为伪,从理论上对“异知”的问题做了说明。《富国》没有使用“伪”字,应是早期的作品,其表述不够准确便不难理解。另外,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往往不对先天本性和后天习性做严格的区分,因为前者需要受到后者的影响,后者又建立在前者之上。荀子可能受此影响,不对能知(知)和所知(智)做出明确区分,一概称之为性也是可能的。但随着后来“伪”概念的提出,将性严格限定在先天本性,而将后天的思虑、实践活动归为伪,从性—伪的角度对心性做出考察,从理论上对能知和所知等问题做出说明。这时“异知”便不能说是性,而只能看作是伪了。
“埶同而异知”一句,“埶同”是假设,是假设一个前礼义的原初状态;“异知”是事实,是能知运用的客观结果。埶,同“势”,指身份、地位。如果在原处的状态中人们身份、地位相同,而客观上人们的认识又相差很远,愚者多,智者少,结果必然是愚者裹挟智者,而智者不得治理愚者,人们因此屈从欲望,“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由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最终必然陷入争夺、混乱之中。而要摆脱混乱,“救患除祸”,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明分使群矣”了。可见,荀子的人性论与礼法论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是由前者推出后者,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
从《富国》可知,荀子从探讨人性之始,便关注到情性和知性两个方面,并从二者的关系思考文明秩序的建立。一方面人有饮食男女的基本欲望,这是基本相同的;另一方面人有“知”,能“可”,可以做是非判断、价值选择,但在实际运用中又有差别。由于欲望不可一味地放纵,客观上也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必须要受到知性的节制,这就需要建立秩序,制定礼义,将欲望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因此,如何看待、处理情性与知性的关系,进而“明分使群”,建构文明秩序便成为荀子人性论的主题,贯穿于荀子思想的始终,并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
那么,《富国》是如何看待性的呢?是否已有性恶的观念?这无疑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富国》的性本来就包括了情性与知性两方面,知性显然不是恶的,相反倒是善的来源。所谓恶只能是对情性而言,用性恶简单地概括荀子人性论,本来就是不够全面的。就情性而言,是否是恶?也需要做具体分析。《富国》认为人都有欲望,如不加节制,“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必然陷入纷争和混乱之中,“争则乱,乱则穷矣”,这与《性恶》的思路无疑又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富国》认为欲恶,或至少是恶的来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害生纵欲”一句,害生即害性。[ 参见杨柳桥《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第224页)、蒋南华《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等。]故在《富国》看来,纵欲不仅引起争夺,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关系,还会伤害到人的内在本性或生理。《正名》:“性伤谓之病。”与此同意。故《富国》的性与欲并不完全一致,其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性虽然包括欲,但只有在一定范围内,不伤害人之健康和生理的欲才可称作是性。故荀子一方面批评它嚣、魏牟的“纵情性”,另一方面又反对陈仲、史䲡的“忍情性”,因为二者都会“伤性”。《富国》对性的这种理解是有根据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子大叔引子产之言:“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五味”、“五色”、“五声”分别代表“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指自然情感、欲望,但“淫则昏乱”,一旦过度(“淫”),反而失去本性,不再是性了。子产为法家早期代表,其思想在三晋一带多有流传,其对人性的理解可能并不是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之后又被诸子学者所接受。如《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又据《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于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注:沉迷不能自制)焉。遁焉,性恶得不伤?”《吕氏春秋》虽成书较晚,但书中内容多取自诸家成说,故实际年代要更早。荀子的“害性”与其一致,反映的应是当时人们对于性的一种理解。
另外,荀子的知应该如何理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自牟宗三将荀子归为儒家智的系统,认为其知只有认知、思辨的功能,而没有道德创造的能力,此说影响甚大,并由此引出第一个圣人或先王如何制作礼义的难题。其实对此问题,《富国》有明确的说法:“知者为之分也。”在荀子那里,分乃礼的基础,知者既然能“为之分”,故礼义乃起于知,人们凭借智能创造了礼义。虽然现实中只有少数人可以明分、制礼,但知作为一种能力是人人都具有的。既然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明分”,它显然具有道德功能,是礼义得以产生的根据,而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能力。不过荀子的知不能凭空创造,它首先要认知,在已知的基础上“知通统类”推出新知,那么最初的先王是如何明分、制礼呢?《富国》对此没有给出说明,这一问题是在以后的讨论中才逐渐得以明确的。
《富国》为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前的作品,这从其对钱币的称呼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战国晚期齐国主要流通的是刀币,有节墨刀、齐大刀、齐明刀等,齐襄王返都临淄后,受秦国的影响,又铸行圜钱,形成刀币和圜钱并行流通的制度。楚国流通的是蚁鼻钱,秦国为圜钱,韩、魏为布币。燕、赵则是刀布并行流通的地区,考古出土的赵国的战国窖藏钱币中,刀币及布币大约各占一半。《富国》与下面要讨论的《荣辱》篇都称钱币为刀布,如“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富国》),“余刀布”(《荣辱》)等,说明两篇文字是完成于一个使用刀币和布币的国家,这个国家只可能是燕国或赵国,属于荀子前期的作品。[ 廖名春注意到《荀子》中有刀币、布币的说法(见《荀子新探》,第17页),但没有用来判断《富国》《荣辱》的年代,甚为遗憾。]另外,从荀子对征收工商税的态度也可以对《富国》的年代做出判断。《富国》称“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主张要征工商税。《王制》则说“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明确反对征收工商税,对山林泽梁也不税,只征收单一的农业税。出现这种差别,应该是因为《富国》是荀子在赵国时的作品,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而法家主张对工商征以重税。如商鞅称“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外内》),荀子虽对此有所保留,提出要“平”,不可太重,但并不主张废除工商税。《王制》则是荀子“游学于齐”时的作品(详下),而齐国有重视工商的传统,主张对工商轻税乃至不税,这在《管子》多有反映,如“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管子·霸形》),“乃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大匡》),“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幼官》)孟子曾游于齐国,也主张“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可能受此影响,故在对工商税态度上前后有所改变。
三、《荣辱》对情性-知性说的探讨
《富国》的主旨不在于人性论,故涉及内容相对较少,《荣辱》由于其内容的关系则对人性问题有较为集中的讨论。《荣辱》与《富国》同为荀子前期的作品,除了钱币的称呼外,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荣辱》的观点与《性恶》多有相近之处,如主张“人之生固小人”,提倡师法之教等等,但《荣辱》与《性恶》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不见使用“伪”字。伪是荀子讨论人性问题时独创的概念,《荣辱》既然讨论人性却不见使用,说明此时伪的概念尚没有形成,其年代要早于已使用伪的《礼论》《正名》《性恶》等篇。《礼论》等篇为荀子中期的作品,而《荣辱》则应该完成于荀子的前期。《荣辱》称: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材性知能”即知性,“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可归于情性,故《荣辱》与《富国》一样,也是从情性和知性来理解人性的。正如日本学者岛一所说,“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有两重属性。其一称之为‘情性’,生而有之,‘不事自然’,肆意放任之则导致社会混乱。其二则被称为‘知虑材性’、‘知能材性’、‘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是朝向既定目的的、人的主体性的、能够认识实践的能力。换言之,荀子的本性论本质上具有二重结构。而后者的‘性’乃是人认识、体认社会规范以及致力于学问的前提条件”。[ (日)岛一:《荀子的本性论——关于其二重结构》,原载《东洋学集刊》第40辑,1976年;中译见《国学学刊》2011年3期。]这种二重结构可以说是荀子人性论的基本特征,也是理解其人性论的关键。当然,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表述《荣辱》与《富国》也有不同之处,最为明显的是《富国》称“异知”,而《荣辱》则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一个强调“异”,一个强调“一”。但这只是侧重的不同,而非实质的不同,若细加推敲,二者又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君子、小人本身就是“异”而非“一”,若说“君子、小人一也”,只能是就“能知”而不是“所知”而言;若指所知,他们实际依然是“异”。后《性恶》称“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知,即智。“士君子之知”与“小人之知”当然是“异”不是“一”。这说明荀子此时已经意识到,虽然现实中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差很远,但又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前者是“异”,后者是“一”。以前称“异知”为性可能并不准确,而且会产生误导,使小人误以为君子“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而“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这显然不利于激发人们的道德自觉,也不利于对民众的教化。因此,在知性的问题上,应该强调的是能知的“一”,而不是所知的“异”,故荀子专门提出“材性知能”以表示之。材,“本始材朴”(《礼论》)之意,有时也写作“才”,《修身》即作“才性”。“材性”以“材”加以修订,表示是一种先天的本性,而与后天的习性有别。“知能”加一“能”字,说明知只是一种能力,而不是能力的实际运用。在“材性知能”上,“君子小人一也”,至于后来的表现不同,有君子、小人之异,则是因为“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这样荀子就从《富国》的“异知”、“异道”转变为《荣辱》的“知一”、“道异”,在人性理论上无疑是一种完善和发展。不过,《荣辱》的“材性知能”虽然说明了君子、小人能知上的“一”,却没有或无法解释其所知的“异”,而现实中人与人的差别不仅在能知,更在所知,故又提出“注错习俗”,试图从举措行为、风俗习惯来说明人们之间的差别。但注错习俗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还是由于人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选择和理解。这样,在说明现实中人们的差别时,《荣辱》便要将能知的材性知能与属于所知的注错习俗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对二者的关系和性质做出明确的辨析,这在下面的文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前面既言君子、小人知性“一”,情性“同”,这里的“一同”也应该包括知性和情性而言。不过说“饥而欲食”之情性是“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固然没有问题,但若说表示知性活动的“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也是“生而有”、“无待而然”、“禹、桀之所同”,则显然会引起争议。故王先谦认为上文最后三句为衍文,当删。[ 王先谦:《荀子集释》,《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39页。]此说被学者普遍接受,几成定论。但近年冯耀明提出异议,认为“此真可谓对荀学理解的一大错误”。其理由是“此段正是用以说明人之本性中有致善成积之能,是先天而内具者”,而“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中的“势(注:亦作埶)”当“是‘执’字之误抄。所谓‘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即以‘注错习俗之所积’之‘积’之成果来自‘执取’之能,亦即由意志抉择而付诸实践之能动性。此能力即《成相》篇所谓‘君子执之心如结’之定于壹的决意之能。这种能力当然是‘人所生而有’的,是‘无待而然’的,也是‘禹桀之所同’的。”[ 冯耀明:《荀子人性论新诠——附〈荣辱〉篇 23 字衍之纠谬》,《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14期,2005年。]按,“埶”与“执”在先秦文献中常有“形近混用”的情况,而《荣辱》既然承认“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那么此段的“凡人有所一同”亦应包括之,具体讲就文中的“势”,指“执取”之能。如果删去了上文最后三句,“一同”的“一”就落空,没有了回应。从这一点看,冯说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一句,不仅提到“执”,也说到“积”,甚至落实在“所积”上。说“执”是“先天而内具者”固然可以成立,但“积”显然是后天形成的,笼统说“人之所生而有也”显然不准确。更重要的是,如邓小虎所指出的,荀子可以承认致善成积的能力是“人所生而有”的,但不会认为是“无待而然”的(冯耀明)。[ 见上文后所附“续篇一:敬答邓小虎先生”。]此正说明情性与知性的不同,情性是“不可学、不可事”,“无待而然者也”,但知性则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必须“有待”而成。荀子在写作《荣辱》时可能对此还没有做细致的辨析,在表述上有不严谨的地方,后荀子提出“伪”概念,并对伪做了“心虑而能为之动”和“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正名》)的规定,包括了能知与所知两个方面,将二者统一到伪的概念之中,这时才对知性的性质和作用做出了理论化的说明。故对于上文最后三句,比较合理的作法是既无须将其当作衍文处理(如王先谦),也不必一定要将其解释得完全合理(如冯耀明),而是认为它是荀子的某一阶段思想的反映,由于对人性问题还处于探索之中,个别表述有不尽恰当之处,这样或许更符合荀子思想的实际。
综上所论,《荣辱》继《富国》之后,从知性与情性两个方面对人性做了进一步探讨,与《富国》一样持一种二重结构的人性论,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有所深化和修正。就知性而言,《荣辱》修正了《富国》以“异知”为性的看法,认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较之后者显然更为合理。《荣辱》还对材性知能的特点做了说明,认为其具有在不同事物之间做出好坏、是非、善恶的判断、选择的能力,可以在“先王之道”与“桀、跖之道”之间做出判断和选择。“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曰:陋也。”(《荣辱》)如果人们见识不广,孤陋寡闻,便会以非为是,以恶为善。这说明材性知能不同于良知良能,只有在经验认知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认识上存在着“陋”,材性知能同样无法发挥作用。“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同上)
就情性而言,《富国》虽然认为欲可以导致恶,但其性是一规范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概念,故尚没有性恶的观念,相反提出“纵欲害生(性)”。《荣辱》在此问题上则较为复杂,一方面称“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乱世,得乱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乱得乱也”(同上)。“人之生”的“生”字或理解为出生,或训为性,若是后者,则其性显然已是描述性概念,指情欲的活动,对性的评价也是负面的,故一些学者往往由此认为《荣辱》已有了性恶的观念。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荣辱》的“情”和“性”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二者并没不完全等同,这在下面一段文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注:当为“不知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注:谷仓和地窖),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注:岂)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
“人之情”指情感欲望,其“穷年累世不知足”;“人之生”即人之性,它虽然也以实现、满足欲望为目的,但却懂得“节用御欲”,具有“长虑顾后”的特点。此性应是知性,可以对情性做出节制、引导。故《荣辱》中两处“人之生”内涵并不一致,从文义上看,“人之生固小人”的“生”恐怕还应理解为出生,强调的是生而如此的意思,人生而所具的各种情欲,使其表现得像个小人。由于后来荀子提出性恶,实际是以情(欲)言性,不再视性为规范性概念,而只是对情欲活动的描述,《荣辱》虽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显然已有向这方面发展的趋向了,故在荀子人性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至于另一处的“人之生(性)”无疑才是荀子所理解的人性,它显然不是恶的,相反荀子称其“几(注:岂)不甚善矣哉!”这说明由于荀子以情性、知性理解人性,情性中的欲虽然会导致恶,是恶的根源,但由于其性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性与欲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用恶来概括性,只是后来性与情(欲)合一,才提出了性恶。至于知性则与恶无关,而毋宁是善的来源。由于荀子的人性是一种双重结构,显然就不能简单地用善或恶来概括。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只能说情性可恶,知性可善。另外,荀子在其早期作品中将情性、知性都称为性,这样也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到底何者才是其所说的人性?《富国》的“害生”应是指规范性的情性,而《荣辱》的“人之性”则是指知性。后来荀子可能意识到这种矛盾,故用性来指情性,而用伪或心指知性及其活动。《富国》《荣辱》都是荀子早期的作品,既用了“异知,性也”、“材性知能”来表示知性,又用“欲”、“人之情”表示情性,有时又直接称“人之性”,实际则是指知性,在概念的使用上是比较复杂、不够一致的,这也是其思想不够成熟、完善,尚处于探索之中的反映。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富国》《荣辱》虽然都提到“心”,但还不是严格的哲学概念。《富国》说到“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严刑罚以戒其心”,《荣辱》也提到“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这里的心都是经验心,实际指情感欲望。稍显特殊的是《富国》的“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此心有意志之意。另外,《儒效》也提到“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此心指思虑,但都不是作为哲学概念使用。这与后来荀子对心大书特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哲学概念的情况大为不同。以往学者谈到荀子人性论时往往称其是“对心言性”或“以心治性”,[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二章“荀子之对心言性”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7页。王楷:《以心治性:荀子道德基础之建立》,《国学学刊》2011年3期。]其实荀子的这一思想也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在其早期作品中心、性对举尚没有出现,其所使用的主要是“材性知能”、“情性”这样的概念。
古籍:《论语》《孟子》《荀子》等。
(清)王先谦,1986:《荀子集释》,《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年影印版。
岛一(日),1976:《荀子的本性论——关于其二重结构》,原载《东洋学集刊》第40辑;
2011,中译见《国学学刊》年3期。
冯耀明,2005:《荀子人性论新诠——附〈荣辱〉篇 23 字衍之纠谬》,《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14期。
金谷治(日),1950:《〈荀子〉の文献学的研究》,《日本学士院纪要》,第9卷第1号。
蒋南华,2009:《荀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涤生,1979:《荀子集释》,台湾学生书局。
李零,2007:《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里西,1990:《〈荀子〉书重要篇章的写作年代考证》,《哲学研究》增刊。
廖名春,2014:《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唐君毅,2005:《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楷,2011:《以心治性:荀子道德基础之建立》,《国学学刊》3期。
徐复观,1955:《释〈论语〉的“仁”——孔学新论》,《民主评论》6卷6期;
2004,《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
杨柳桥,1985:《荀子诂译》,齐鲁书社。
杨泽波,1995:《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